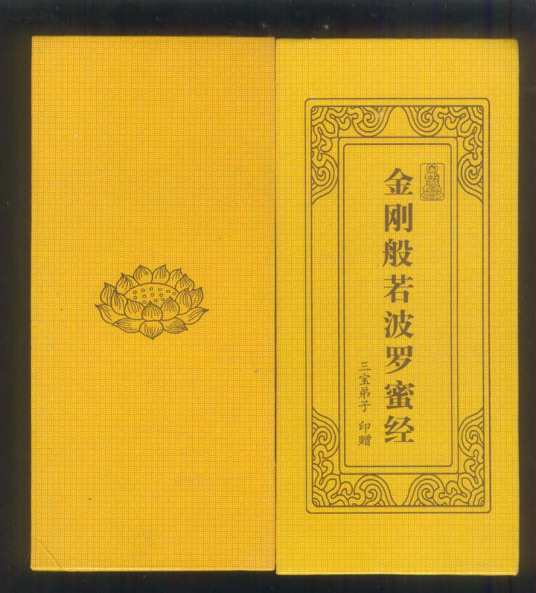uploads/content/2022/june/8d07a9bb127c251d57a2a7ade6d8dbd3.jpg" />
《金剛經》在中國的歷史上,自從由鳩摩羅什法師和玄奘法師翻譯過來之後,沒有任何一部經典像《金剛經》這樣在中國根深蒂固,廣泛弘揚。雖然在一些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來看,《金剛經》具有很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哲學性,但是並沒有因此而被廣大民眾所漠視。在中國廣大的區域中,不管是歷史上,還是現在,廣大民眾都有一種普遍的意識,就是認為讀誦受持《金剛經》能夠薦亡積福。在歷史上,有很多文化人以抄寫《金剛經》為人生的幸事。因此,在唐代書法界出現了一種抄經熱。在抄經熱興起以後,中國字的形體中出現了一種寫經體。在杭州十五洞的摩崖石刻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刻的都是有關《金剛經》的內容。泰山可以說是一座文化的山,在那些摩崖石刻上,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刻的都是《金剛經》的內容。其中有一處人文景觀,就是泰山的經石峪,用顏體字(每個字一米見方),把整部《金剛經》都刻在了這個山谷里。除此以外,在中國的四大名山、四大石窟,隨處都可以見到有關《金剛經》的內容。這些文化人,把他們理解的《金剛經》的某些經文刻寫在石頭上,其用意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認為這是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另一方面,他們也想讓更多的人由此而了解《金剛經》,悟入《金剛經》。
關於《金剛經》的版本,在中國為保存《金剛經》的版本,有著非常多的典故。比如,如何將《金剛經》刻寫在石板上,藏在密室中,經過幾百年或上千年以後,又被一些高僧發現。在我對《金剛經》進行研習的時候,其中有一位日本人使我非常感動。他在唐代的時候,把《金剛經》刻在了鋼板上,帶到了日本,後來,當中國這個版本消失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在日本又發現了這個版本,使它重新又流傳到中國來。
我講這些,就是想以歷史事實來說明《金剛經》與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座的各位,我們今後修學的道路還很漫長,要接觸大量的經典,在沒有研習經典以前,有許多外圍的東西需要大家了解。所以,我今天在這裡講的目的只是想給大家起到一種導讀的作用。
首先,我對經典的“經”字作一下解釋。“經”字具有準確的內涵和外延。按傳統的講經方式,“經”字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詮釋。經的第一個含義,有方法和途徑的意思。經的第二個含義,有勝載義。比如現在我給大家講《金剛經》,聯繫著大家的生活來講,這是一種方便。我們各位在提問的時候,或者和我交談的時候,也有很多思想,但我們的思想是散亂的,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作為一部經,它是完整的一個思想體系。勝載義,有收藏的意思。就是說它把許多閃光的思想收藏在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裡面了。因此,我們往往把經稱為藏經。藏,也是收藏的意思。經的第三個含義,有不可更改義。任何一種宗教或者學派,把一種認為是不可更改的權威性的書,稱為經典之作。所以,並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稱之為經的。佛教的經典,是佛陀的弟子把他的教法結集後,以固定的形式流傳下來的,是不可以更改的。另外,像道教老子的《道德經》也是這樣,任何人沒有權力進行刪改。後人所能做的,只是對經典的注釋和論述。唯有這樣,佛陀的思想雖經流傳了兩千五百四十年,卻還能保持它的原貌。也使我們後人通過讀經,能夠直接地了解佛陀的全部思想。
在過去,翻譯經典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在西安慈恩寺,以玄奘法師為首,通過國家嚴格篩選出的上千名高僧聚集在一起,他們在對經典進行翻譯的時候,有時對某一個字的確立,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辯論,力爭用最准確的文字,把它融進全部的經文之中。而現代人在翻譯經典時,已經很少有人能這樣嚴謹了。隨著我們對現代化運作工具的掌握和對現代媒體的把握,有些人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讀懂這些具有深奧道理的經典,也有的人是出於功利之心,於是就把這些佛經譯成白話,然後輸人電腦,或是著書出版。我覺得這種方法很值得商榷。因為中國的文言文,它的句式結構是非常嚴格的。除此以外,它的思想內涵是非常豐富的。當我們輕描淡寫地把佛經譯成現代的語言時,很可能就貪污了佛陀本來的思想。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當然,我談這個問題,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夠推陳出新來做這項工作。而是說,我們在做這項工作時,一定要本著非常嚴謹的態度。本來在佛法傳入中國這一漫長的歷史中,翻譯的時候,語言就有很多的障礙,就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如果我們現在的學者不能很嚴謹地對待這件事情,那麼就會貽誤後人。過多少年以後,人們恐怕就很難看到佛陀思想的原貌了。
古往今來,講《金剛經》的人非常多。但是,由於每個人對佛法的悟入有淺深偏圓的區別,所以對《金剛經》的解釋也各有不同。有個比喻說,兔子到海邊去喝水,它回來後,仙人問它海有多大?它說,海就像我肚子這麼大。鹿也到海邊去喝水,它回來後,仙人問它海有多大?它說,海就像我肚子這麼大。大象也到海邊去喝水,它回來後,仙人問它海有多大?它說,海就我肚子這麼大。仙人非常嚴肅地告訴他們說,海就像海那麼大,你們三個的肚子都是很有限量的。我們今天面對佛法的大海,就應該反省自己,我們的經驗、閱歷、心量和智慧都是很有局限性的,我們以自己有限的尺度去衡量佛法,我們所能認識到的,已經不是佛法的本然了。當我們以自己的限量去講解佛法的時候,混入了很多我們自己雜染的思想和境界。所以,當我們在弘揚佛法時,首先應該取一種非常嚴謹、慎重的態度。我今天在此給大家講《金剛經》,只能作為一種導讀,也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塊敲門的磚。使大家知道,《金剛經》是一部專門闡述有關人類智慧的經典。《金剛經》不但是禪宗的寶典,更是所有修學佛法的人都應該了解和親近的法寶。佛陀說:“智慧以為母,方便以為父,諸佛大導師,無不由是出。”一個學佛的人,不管你學任何一個宗派,任何一種法門,智慧是我們唯一的導師。如果沒有智慧的話,你的所學將失去航向,你的所修將是盲修瞎煉。而我們在教化眾生的時候,就需要各種善巧方便。三世諸佛和一切祖師、導師都是由此而產生的。所以才有這樣的說法:“佛是覺悟了的眾生,眾生是迷了的佛。”
釋迦牟尼佛活了八十一歲,在他講經說法的四十九年當中,用了二十三年時間講般若。般若是梵文的音譯,中國人在翻譯的時候,沒有相應的文字來翻譯這兩個字,為了保持佛陀講經說法思想的原貌,就以音譯的方式把這兩個字保留了下來。這也說明在最初譯經時,我們的先師大德們是非常嚴謹的,在實在沒有相應的文字加以准確的翻譯時,絕不勉強翻譯。有的人,後來把般若譯為智慧,但意譯為智慧,往往會被中國人理解為聰明。因為中國文字的聰明與智慧似乎沒有太大的分野。在這裡,我先講講聰明和智慧的區別。所謂聰明,是沒有定力,靠我們第六意識的分析、判斷,患得患失,在這方面所用的功夫,表現為聰明。在文言文中,把聰明解釋為耳聰目明。人老了的時候,眼花耳背,誰也不會稱老人為聰明。只有對年青人,才稱之為聰明。所謂智慧,不僅僅是知識,知識能增加我們對事物外部的感知和認識,智慧非常近於大智若愚這種思想。就是說,只有生髮了我們內在的潛能和智力,把心上的蒙塵抹去的時候,原來本體的東西才可稱為智慧。如果用西方的思維方式給大家解釋,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不但能夠對事物的外部進行分析判斷,而且能夠對自己進行迴光返照;不但能夠知道現象世界是如何建立的,而且能夠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也就是所謂的雙照雙觀,才可稱為智慧。因為在中國沒有一種與般若相應的詞,所以就勉強把它意譯為智慧。
佛陀在講經說法的時侯,他把我們人類的智慧看得十二萬分的重要。但是可悲的是,自從佛法傳入中國以後,在中國的民眾中,每當談到佛法時,總是把那些死亡、灰暗、落後、消極厭世的東西與佛教緊緊聯繫在一起。所以,當許多法師在講經說法時,總是一再地強調佛教是智信而不是迷信。但是,有人不分青紅皂白地總是把佛陀當初只是為了使人樹立正知正見的這種方法稱為迷信。當然,我們也反省自己,在佛法的流傳當中,因為兩種文化的互相交融,我們民俗中原有的一些東西也滲透進佛教中了。
佛陀用二十三年的時間講般若,譯成漢語的般若經,僅玄奘法師一人就譯了六千七百二十四卷。佛陀所有的教化用經、律、論三藏十二部來囊括。現在我們的藏經樓里的經書,以我這樣的勞力搬上一星期才能搬完。很多人一聽,可能就覺得害怕。這麼多沒有標點符號的線裝經書,我要讀的話,哪年哪月才能讀完呢?今天我們在這裡講般若,就是為了消除大家這種迷茫的。
現在翻譯成漢文的有關智慧的經典是六百卷,叫《大般若經》。佛陀在講經說法時,他的思維是非常嚴密的,絲絲相扣,儘可能地讓我們從文字上直接領會他的思想,而不要產生歧義和誤解。在六百卷《大般若經》中,極為突出地表現出其思想的嚴密性。佛陀每講到一種思想時,總是把別的思想還要重複一遍。當我初次接觸《般若經》時,我下決心一定要把它讀懂。但是,當我讀了幾天後,我就不想再讀了。因為其中許多經句是來回反復地講,而且其思想性是非常嚴謹的。我們一般人的思想是非常鬆散的,所以面對很嚴謹的思想,讀多了就會感到很累,很乏味。因此,我第一次讀《般若經》就沒有堅持讀完。過了一段時間,反思了一下,覺得自己身為一個出家人,連佛陀般若類的經典都讀不下去,當別人如果說我是迷信的時候,我就很難說得清楚了。於是,我再次發願要把《般若經》讀懂。這次再讀,雖然比前一次有些進步,但依然還是沒有讀懂。也就是說,《般若經》的思想體系非常龐大,有很嚴密的邏輯性,有很深邃的思想內涵,這對我們一般人來說就會形成一種很大的障礙。我認真反省自己,覺得這就是自己業障的反應,包括文字上的障礙,所有這些障礙,使自己不能深入到經典當中去。我講的這些感受,今後各位在讀經的時候,或許同樣會碰到。
六百卷《般若經》雖然非常難讀,但一個學佛的人又需要這種智慧,這是一個矛盾。因此《般若經》被翻譯過來後,祖師們觀察時節因緣,他們把六百卷《般若經》第九分的“能斷金剛”單獨提了出來,出了一個單行本,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剛經》。《金剛經》被提出來在翻譯的時候達到了信、達、雅。也就是說,如果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金剛經》的文字非常優美,節奏非常明快;如果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金剛經》的哲學含量非常豐富;當我們以《金剛經》作為修學的指導時,它確實可以使我們明心見性。《金剛經》總共只有五千二百七十四個字,但是洋洋五千言卻有著無窮無盡的寶藏。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窗口,深入到佛法智慧的大海中去。《金剛經》主講的就是般若,般若就像是一把利劍,如果我們真正能夠把《金剛經》讀懂了,我們再讀別的經典,別的經典的思想障礙和文字障礙就會迎刃而解。
如果一個學佛的人沒有抓住般若的思想,沒有以智慧為先導,十個人有九個會差落。尤其我們現在的時代,是一個科技昌明、信息爆炸的時代。如果我們沒有智慧的話,很可能就會迷失了自己。當我們深入般若以後,以所掌握的智慧來看問題的時候,既可以使我們站在每個角度去看清楚問題的關鍵所在,又可以使我們不被牢牢地局限在所站的角度上;既可以使我們深入到每一個層面,又可以使我們不拘泥於每一個層面。
佛有十大弟子,每一個弟子都有自己能力上的第一。在整部《金剛經》中,佛陀都是與“解空第一”的須菩提進行問答。在這些問答中,集中地展現了佛陀所有的般若思想。佛陀的這種展現,並不是像我現在這樣依文解字地給大家講解,他的智慧完全是從自己的毗盧性海中款款流出,也就是說心中原本就有了這些東西,他只不過以各種角度描述給我們。
既然般若思想這麼重要,那麼修學禪法的人又是怎麼運用般若思想的呢?整個禪宗發展史是很漫長的,我只能粗線條地給大家勾畫一下概況,使大家明白般若思想與禪宗的思想是水乳交融的。從初祖達摩一直到四祖道信以前,這一階段一直是以般若為修禪的憑證,以《楞伽經》為印心的法本。到了四祖道信,他在湖北黃梅弘揚禪法的時候,就是以《金剛經》為他的門人來印心了。就是說判斷一個人是否開悟了,是否明心見性,就是以《金剛經》為印心的憑證。《金剛經》的印心法門,到了五祖和六祖時,這種傳法因緣表現得就更為顯著。也就是說從初祖到六祖,般若思想就像一條橫線,對整個禪宗思想史起著一種貫穿的作用。因此,六百卷《般若經》和其中的《金剛經》在禪門中被稱為禪宗寶典,是所有修學禪法的人必須要修學的功課。
《金剛經》是佛陀以一種方便把他的智慧形象化了,他把這種根本的智慧比喻為金剛。金剛以它奪目的光彩,堅硬鋒利的質地而獨尊於各種寶物之中,它被稱為寶中之寶。佛陀以金剛比喻般若智慧,說明這種智慧如金剛一般鋒利無比,堅硬無比,無堅不摧。這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坐標,只有以《金剛經》的般若智慧為唯一的標準,才能分辨出我們的世出世法是否圓融,我們的思想是屬於聰明,還是屬於真正的智慧。
“般若彼羅蜜”的意譯,就是用大智慧度我們過彼岸。有人曾問我,有此岸和彼岸嗎?此岸和彼岸是佛陀所證悟的本體,是離開語言文字和名相的,是一法不立沒有言說的。但是,我們現在卻看見這麼多語言文字的經典。這一切都是因為一種方便,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其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因指見月。比如我用手指指天,說天上有一個月亮,聰明的人就會因為我的指點去看月亮,而愚蠢的人只會牢牢地盯住我的手指說,沒有月亮呀,並讓我拿出月亮給他看一看。所以,語言文字只是一種方便的引見,它可以起到一種溝通的作用,而覺悟的境界是語言所不能夠完全表述的。因此,佛在講《金剛經》時用心良苦,他往往是邊講邊掃。就像一個人從雪地上走過,他要想抹去留下的腳印,只好邊走邊掃。然而這樣一來,腳印雖然可以抹去,卻還會留下掃帚的痕跡。所以,很多祖師講到語言文字與開悟境界的關係時,往往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開悟的境界不允許我們在語言文字上去求,但又必須去講,因為我們常人善於思辯,善於用語言文字去理解事物。有智慧的禪者往往是通過某種途徑,把我們引到山高水長的地方或是沒有遮蔽的地方,然後指給我們說,那就是月亮。就是說用盡種種方法,只待你自已去開悟。比如說舉起了拂塵,砍掉了手指,拳打腳踢,乃至呵佛罵祖,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我們放下對語言文字的執著,當下悟到心的本體和法界的真如。
是否有此岸和彼岸呢?當我們產生煩惱的時候,就有了此岸和彼岸;當我們當下承當,解脫、清涼、自在的時候,就無所謂此岸和彼岸。此岸和彼岸是一種文字上的建立。為什麼建立此岸和彼岸呢?就是為了表示法有兩個。平常我們都說佛法是不二法門,而我在這裡講法是兩個,這就是指世間法和出世間法,或者聖人的思想和凡夫的思想。聖人取得覺悟之後,為了使我們明白我們同他的差異,他就把解脫的那面叫做彼岸,把凡夫的煩惱、爭名奪利、無明暗昧的世界叫此岸。這是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佛是覺悟了的人,當我們各位也能放下、自在、解脫、輕安的時候,我們也是佛,那我們與佛也就一體不二了。當大家不明白我現在所講的這些道理,才有著老師和學生的分野;當各位已經掌握了這些思想,我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這種時候也就無所謂老師與學生了,那麼我們就是一體,而不是兩個了。我認為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是非常圓滿的,既認識到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又領悟到它們之間的同一性。由此我們也可以悟到,在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是相依共存的。如果我們僅僅看到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時,只會增加我們的煩惱;當我們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的同一性時,我們就會產生理解。比如在生活中,當一個人的品格與我們發生衝突時,我們要學會自他相換,站在他的角度來看我們自己,領悟到他與我們的同一性。只有這樣,我們的胸懷境界才會更寬廣,我們的煩惱才會淡化。如果我們不具備這種不二法門的方法,我們就是想解脫,想增長自己的智慧,想拓展自已的胸懷境界,即使有著這樣良好的願望,也是難以達到。所以,認識事物的方法非常重要。
我們一般人腦了里都是裝滿了概念和定論,因此在深入經典的時候,第一大障礙就是所知障。我們總是拿學過的東西和已知的概念為尺度來左右地衡量所看的經典。當看到經中所說的話符合自己的思想時就接受,否則就排斥;或者總是想在生活中找出它的真實憑證。前兩天濟群法師講到,說有一位哲學家曾經說過,人類社會自從建立以後,我們人就把自己作為唯一的尺度來認識這個世界。這種描述非常准確。有一位叫海默爾的物理學家,在他的一份物理學答辯的扉頁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今天所有科技的研究成果,只是釋迦牟尼玄記的開始。”玄記就類似於預言。他並且說:“以人為尺度建立起來的這個社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有很多做學問比較客觀的人,他們常常談到人的局限性和時代的局限性。佛陀與我們有這麼久遠的時空跨度,他又是一個覺悟者,我們對於覺悟者的言行和思想如果用凡夫的心去分析判斷的話,怎麼可能得到一種客觀而公正的結論呢?所以,我們學佛時常常強調要放下以往的知見。就像一隻茶杯要倒入甘露,我們必須先把茶杯里的東西倒空,並且把它清洗乾淨,然後再倒入甘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品味出甘露最純正的滋味。如果我們根本不願把茶杯里原有的東西倒空,直接就倒入甘露,怎麼可能品嘗到甘露原本的滋味呢?
出於對聖人思想境界的尊重,我只能把我所講的《金剛經》作為一種導讀,給大家提供一種參考,而不能作定說。因為我的學識、智力、心量和修為等等都還是很有局限性的,雖然我是出家人,但是我坦白地告訴大家,我和一般人一樣是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慾,有人的局限性,甚至有很多致命的弱點。尤其在涉及到佛陀的經典時,我覺得我的智慧太有限,不能以一種使大家更易理解和消化吸收的方法使大家更直接地進入佛法。因此講的時候,我感到很吃力,只能以一種談心的方式與大家進行對等的交流。
《金剛經》所有的思想內容,我把它歸結為三個層面,也就是三種般若,即三種智慧。
我們學的所有的書本知識,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知識不經融會貫通的話,就具有了文字般若。這種般若是世間的智慧。一個學佛的人,在學佛的初級階段,面對浩如煙海的經典,每部經典的內容又都是文言文,所以我們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文字上的障礙。如果我們連文字的內涵和外延都不能知道,那麼這樣讀經,就像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所以說佛法不違世間法,一方面知道世間的文字是假名安立,另一方面又不壞世間相,這就充分地肯定了文字安立的必要。就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熟練地掌握語言文字,他靠近智慧的速度就會加快。
在禪門下,有很多人會產生一種很深的迷茫和誤解,因為禪宗說不立文字,並讓我們把所有的文字都放下,但禪宗的歷史所表現出來的卻是另一種現象,自佛法傳入中國在唐代形成八大宗派以來,禪宗所結集的語言文字是最多的。比如禪宗的公案有一千七百多條,禪宗的語錄,各種燈錄非常之多,這就足以說明文字本身非常重要,而不是像有些人片面地認為禪宗不需要文字。
大家現在所學的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都屬於世間的智慧,世間的智慧重心是以人為主體,通過這種知識的學習,使我們了解掌握以及推動外部事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佛經也運用語言文字,其目的是讓我們破除煩惱,放下執著,得到解脫。同樣是語言文字,世間的智慧是引導人向外,佛法的智慧卻是引導人向內。當我們強調世出世法圓融無礙的時候,我們往往說是在方便的時候,世間法的這些語言文字以及這些音像設備是很重要的,但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佛法的特質。當我們在強調佛法的特質的時候,並沒有否認我們運用人類社會的語言來完整的表述佛法。
文字般若,如果用一句話來高度概括的話,這就是:語言文字本身雖然不是真理,不是真理的本體,不是法界真如,不是涅槃的實體,但是語言文字可以使我們由此而領悟到真理本身,因此我們稱之為文字般若。
觀照智慧與我們的人生實踐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為什麼說知識並不等於一個人的修為呢?在生活中我們會發現,有一些人雖然知識非常豐富,具有很高的學位,但心胸卻非常狹窄,很自私,很貪婪,這就因為這些人所掌握的知識只是前人的一種經驗,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些經驗吸收轉化為自我的經驗。所以在認識事物的時候,他們的眼睛只會往外看,而不會內視,不會迴光返照觀察自己當下的心念,也就不會注意到自己內心的局限性。這就是學與用的分離。所以說知識與人的修為不能夠劃等號。
另外,也有些人雖然沒有文化,不善言辯,不能講出那麼多的道理,但是他們的胸懷卻是很寬闊,很坦然,很正直無私。當我們靠近這種人時,就能夠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被他人格的魅力所感召,這種人有時就不需要語言文字為表達。我們對於佛法的修學就應該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文字上,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語言文字上,停留在思辯上,那也只能叫做佛學,不能叫做學佛。所謂佛學,就是不管你信不信仰佛教,只要是用一種客觀、平實、考據、推理的方法去了解佛教,就可以稱為佛學。而學佛就不僅僅需要明理,明白佛教的歷史和教理,更在於以佛的教理為指導,克服自己的習氣,消除自己的業力,像佛陀那樣走向徹底的覺悟。也就是將佛法的道理落實在自己的當下。使原來沒有智慧的思想言行趨向智慧,使原來狹隘的心胸趨向寬廣,這才叫做學佛。因此佛學與學佛之間雖然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但根本的落腳點卻是不同的。佛學僅僅停留在對佛法的了解上,學佛卻在於使佛法落實在生命的每一當下。如何使佛法落實於生命的每一當下,這可分三點來談。
首先,談談佛教的戒律。戒律是律學,是一個很龐大和完善的體系,它既有原則又有方便,有很多複雜的辯證關係。我今天並不想給大家講律學,在這裡我只告訴大家最重要的一條,即佛教所有的三皈五戒、十善、比丘的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的三百條戒,種種的戒律歸根結底都是用來自律的,是讓我們掌握這種方法用來要求自己,而不是讓你拿著戒律去掃描別人。這就是與社會上其它的哲學、思想、法律最大的不同之處。社會上的法律叫做他律,只有道德的規范和佛教的戒律叫自律。他律和自律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有著千差萬別的內涵。比如有的人與別人發生了矛盾,於是躺在床上想像著如何把對方置於死地。你躺在床上如何去想,沒有人管你,因為你內心的活動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管。但是它可怕就可怕在這一點,因為任何一種行為都是源於最初的一念,一旦這種念頭在你心裡醞釀成熟付諸於行動造成了社會或人身的傷害的時候,公安人員、司法部門才會出來追查這件事情。大家想一想,這是不是太晚了?因為已經既成事實,即使是追查,逮住了這個人可以繩之以法,以警世人;若逮不住這個人,就可能使這個人更加變本加厲地危害社會。所以我們今天弘揚佛法,張揚它的道德,顯然是可以彌補法律之不足的。法律只能治末,佛法卻可以使我們自覺地去治本。社會上很多行為的準則就在於本末倒置,包括我們對於事物的認識。一旦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本末倒置之後,就不可能對事物產生一種正知正見。
第二點,談談佛法對人心的改良。佛陀講的所有的經都是定學,就是告訴我們一種修定的方法。使我們能夠在紅塵熱惱中迴光返照自己,照看好自己的心念和行為。現在的社會,恰恰是有很多人沒有時間反照自己,而且根本不懂得如何反照自己。因此,在名利得失面前就很容易迷失自己。心被外在的一切所迷,就不能夠作自己的主人,就成了被外物所轉的奴隸。
第三點,談談佛法對人的智慧的開發。佛教所有的論都可以稱為慧學。因此經與論用三個字概括就是戒、定、慧三增上學,或叫三無漏學。我今天講的重點是般若,就在於智慧。佛教所有的論幾乎都是讓我們確立對人生和宇宙的正知正見。當我們有了正知正見以後,所有的事情就好辦了。
這幾天大家爭論的熱門話題就是佛法與科學的關係。我聽了以後真是大汗淋漓,因為任何一種偏執的看法都可能導致我們信仰的退失。首先,我覺得我們大家要形成一種共識,就是科學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不管它鋒利也好,遲鈍也好,關鍵在於運用工具的人。就是說科技的昌明,物質的豐富,並不是導致人們道德淪喪、核戰爭威脅等等人類敗壞行為的根本原因。有一位同學講得很好,他把科學比喻為一把刀子,說醫生可以運用它治病救人,歹徒卻可以使它成為殺人的工具。我覺得這才是正知正見。對於科學,我們如果能夠駕馭好它,使它造福人類,改善環境,科學就起著使人類邁向進步的良好作用;如果我們不能夠駕馭好它,使它用於戰爭。用於破壞資源,破壞環境,那麼就使科學可能成為導致人類毀滅的兇器。另外,科學本身有其自身在發展中的局限性。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正反映了我們人類自身的局限性。我們每個人在研究學術的時候,有每個人自身的局限性;我們人類在整個文明發展的進程當中,有人類自身的局限性。人類的局限性,比如表現在民族的狹隘性,本位主義,以及集困的利益,這些都屬於一種擴大的自我。人們為了保全一種擴大了的自我,因此就產生了戰爭。戰爭產生之後,誰都希望自己掌握一把最鋒利的武器,這種時候,和平只是一面沒有實在意義的旗幟。誰都一手高舉著這面旗幟大聲疾呼:“我是為了和平!”而另一隻手卻在急著磨快自己的刀。這就是我們人類自我的局限性。佛法的智慧就是耍我們沖破這種局限性,打開我們的眼界,擴大我們的心量。
面對科技所裝備起來的強大的軍事力量,有的人可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用宗教的力量去呼喚和平是否顯得太蒼白了?表面上來看,宗教是顯得很蒼白,但是宗教卻可以喚醒人類內在的智慧,這種智慧一旦被煥發出來,其潛力將是無窮的。然而要想沖破人類自我的局限,就如同要改變人的本性一樣實在太難。作為一位弘法者,雖然我們明明知道這種現實的艱難,明明知道我們個人力量的有限,但是我們還是要竭盡全力,就要像杜鵑啼血一樣,啼破了嗓子,流出了血,依然不停止我們對於人類的呼喚,對於世界和平的呼喚。
我講觀照般若,就是希望大家學習佛法之後,要運用佛法的標準建立起一個思想的坐標。如果這個坐標是清晰的,在社會生活當中,當我們自己的利益與別人發生衝突的時候,就要靜下心來用這個坐標去衡量。我個人學佛之後最大的受用,就是學會了用緣起法來解釋生活。
我原來是一個脾氣非常急、很主觀又很執著的人,有一天,當我突然回過頭來想看看自己走過的路程,這時我通過文學詩歌的境界,以及看了八大山人的繪畫,看了《五燈會元》,再看了佛教的一些小冊子,這才發現我以前那些狂妄的辯論,那些對別人不屑一顧的行為,是多麼的幼稚可笑。因此,學佛以後我開始用緣起法來看待人和事,看待自己的名和利。當名譽和利益當頭的時候,我明白那是某種善緣的相聚,而這種善緣的相聚是沒有恆定性的,它必定是要過去的,因此我的心就不會為它所動。當我處在生命的低谷,被別人謾罵,不被人理解,在我感到很痛苦,很失意的時候,我明白這是某種逆緣的相聚,它必定也是要過去的。因此我就提醒自己保持一種平常心。當然這種保持不是消極的等待,因為我明白我不能夠左右這個社會,不能左右別人,我唯一能制約和主宰的只是我自己,所以,我就從我自己做起。
有一位法師說過樣的話:現代的人穿衣服是穿給別人看的,而不穿給自己。這句話表面看來雖然很通俗,但確實是一針見血,很有份量。也就說,找們現代人在做人的時候,往往是向外關注得太多了,總是在想,社會如何承認我的價值?別人會怎麼看我?而不是去思考我應該如何走好當下的每一步?
就具休的修行來說,在座的很多人接觸佛法之後,都希望自己由迷而悟,希望白己早日脫離煩惱,早日解脫自在不二。但是他不願意打坐,甚至不願意聽講座,因為他覺得佛法講來講去反反複復總是那一套,讓他感到很乏味。他從來就沒有反省一下,在現在這個社會中,我們能夠有多少這樣的機會來聽聞佛法?印度有位高僧叫阿姜查,他寫了一書叫《森林裡的一棵樹》,他以一種形象的比喻把自己內心的體驗以及一些深奧的修行境界通俗地表達出來了。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路邊有一個黑洞,從這裡路過的人們都很好奇,每個人都把手伸進去想探一探這個洞有多深?每一位探洞的人都說這個洞太深了,但從來沒有一個人說我的手臂太短了。我在與許多同學探討佛法時,我也發現許多人都說佛法太深奧了,而不是說自己的智慧太有限了。
今天這個生活禪夏令營,首先就講禪,禪是佛教的精髓。一般的解剖學,首先是把皮膚這個層面解剖開,然後深入到脂肪、肌肉、骨頭,最後才是骨髓。我們這個夏令營直接就把佛教的精髓展示給了我們大家,所以許多人有這麼多的疑問非常合乎情理。原因就是我們從一個橫截面直接地就深入到了佛教的最里層,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從佛法最外層的基礎知識一步一步了解佛法的整體概況,最後才深入到它的實質。當我們一步就深人到佛法的實質時,幾千年的思想濃縮在一起,就像一塊風乾了許久的饅頭,我們沒有鋒利的牙齒幾口就把它啃掉,更不用說消化了。也就是說,我們不具有鋒利的智慧一下子就能把佛法的實質完全弄懂。因為許多人咬不動這麼堅硬的饅頭,或許就會抱怨這塊饅頭太堅硬了,而不是反省自己的牙齒是否太脆弱了?
我今天面對佛法智慧的大海。我不敢做定說。因為一個人在沒有開悟以前,他所講的法只能說是靠近佛法,與佛法相似卻不等同於佛法。比如佛在《金剛經》中提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很多人沒有學佛以前就知道大千世界的概念,但是並沒有用自己的肉眼,或用自己的修道,或用科學的方法,如實地認識這一概念。佛陀經過苦苦修道,當他治心一處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三千大於世界是當下證到的。當他看到我們的宇宙世界是由無數的星體、無數的星系組成的時候,就用了三千大千世界這一概念加以概括。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實際上是一種虛指,並非實數。而有些人卻依文解字地認為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三千個星球。另外世界的概念,過去、現在、未來這種時間的概念稱為世;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這種空間的概念稱為界,時間與空間的總體稱為世界。這一概念的形成,是佛陀通過修道以一種直接悟入的方法,所得到的現量證量。而我們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三千大千世界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態呢?找們只能站在科學家的肩膀上去認識。科學家是通過可操作的工具進行實驗的方法逐漸地認識這個世界,我們卻只能通過科學家的認證產生認識,所以我們是用認識的方法認識世界。
各位通過參加生活禪夏令營,回去之後,如果要把對佛法的認識落實到生活的實處,其中很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掌握佛法的真義。並把它作為我們行為的坐標,以這個坐標為準則,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尤其是我們年輕人,因為血氣方剛,又有自身很多不好的習氣,更應該自我剋制,培養自己的忍耐力。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業力,講到業力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感到困惑,覺得業力這個概念很抽象。所以,我先講一下業力在教義上的內容。比如我們在講話的時候,有的人會以為話說過之後聲音消失了,話的作用也就跟著消失了。其實不然,無論我們講話的人,還是聽話的人,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都會埋下這話裡面所含的思想的種子。類似的話講多了,或者聽多了,也就會給我們意識里這種思想的種子熏染成熟了。就是說,我們身、口、意每一次的言語、行為、起心動念,都會在我們的意識深處打下深探的烙印,這種烙印的積累就是業力。而我們的身、口、意又深受這種業力的影響,並順著這種業力的作用一直延續不已,就像一列順勢而行的火車。當我們學習佛法之後,意識到自己以前的人生觀、認識論都是錯誤的,就應該把這個車剎住。當我們突然剎車之後,這時候車的慣性還在推著我們向前走,這種余勢使得我們不能夠自己做主,在我們的思想深處產生兩種不同勢力的強烈碰撞,讓我們感到很痛苦。為什麼會這樣痛苦呢?這就是我們內心無明的業力與我們現在所學到的佛法知識產生碰撞之後的必然反應。
在文革批判孔子的時候,有一位老儒學家曾經說過:“我們有幾個人取得了批判孔子的資格呢?”結果他也受到了批判。對我們現在所講的佛學思想,也有一些人妄加批判和指點。在你批判、指點這些思想的時候,你對自己是否首先有一種正確的評估呢?對一種觀念當我們沒有全面了解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虛下心來,放下所有別人對這一觀念的認識,而直接地去了解這一觀念的思想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取得了品評它的資格。
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的認識是有限的,面對無數的知識,而對無限的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非常重要,更重要的還在於這種方法的背後所應該具備的一種包容的心態。如果一個人沒有一種虛懷若谷的人生態度,是不可能成就一種賢聖的境界的。《金剛經》上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就是說賢人和聖人也是有差別的,他們的差別是境界上的差別。而我們常人之間更是千差萬別,這種差別主要是品行上的差別。所以,學會虛懷若谷,這不僅僅是宗教上的一種情操,更是我們做人的一種情操。正如太虛大師所言:“仰止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我們學佛的目的是要轉凡成聖,但是我們不可能直接超凡入聖,所以太虛大師以一種菩薩的精神給我們搭了一個梯子,讓我們先從做人這一最基本的階梯邁步。這就使一些人產生了誤解,以為佛法等同於我們做人的某些道理,認為佛與凡人之間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其實佛與凡夫是有分野的,佛是大智慧、大自在、大無畏、大解脫的人。我們凡夫在沒有覺悟之前,我們不能自已做自己的主,我們的心是迷惑的,染污的。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這隻是一粒種子,如果你不把它埋在適宜的土壤里,不給它充足的陽光、充足的養分和充足的水分,它也就不可能發芽、更不會開花、結果。
有句話叫“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當我們明白了佛法的道理之後,我們就應該牢牢地看護住我們自己的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個起心動念都是我們行為的一個因,所有這些起心動念的因都是互相雜染的。為什麼說菩薩畏因呢?菩薩在因地的時候,他知道因就像種子似的,能引發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合抱的大樹都是發之於毫端,也就是說,任何一種事物它演變成一種根大的局面都源於最初一念心的波動。
在我們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有些人就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概念再縮小,就縮小為錢。所以就流行一句話叫做:“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在說明這個問題之前,我首先要聲明的是,對於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乎,提高社會物質文明的水平,我是深表贊成的。因為人們不能擺脫物質生活的困苦,也是一種苦。佛教要人離苦得樂,其中就包括擺脫貧困的物質生活給人們造成的困苦。佛法中說,身安則道明。只有安頓好自己物化的生命,才能使道心安立。如果沒有蔽體的衣服,沒有千萬間寧靜的佛剎道場,佛法也無法安立於世間。這就充分肯定了物質文明的重要性。但是,當我們不能駕馭金錢,被它所奴役,為它道德淪喪,偷盜、搶劫、貪污、犯法,以至父子、兄弟之間為了金錢的利益大動干戈,這不是很可悲嗎?
另外,當談到錢,談到貧富的問題時,有些人就誤認為富人彷彿都是比較虛偽,比較自私的,而窮人都是比較善良,比較誠實的。這種認識其實是很錯誤的,人的品質並不能以金錢的多少、貧富的差別來衡量,而在於人的貪欲、私心是否強烈。如果是一個很善良的人,當他很有錢的時候,他可以用錢去做更多的善事;當他很窮的時候,同樣可以隨遇而安。如果是一個很貪婪自私的人,當他很有錢的,他就會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當他沒有錢的時候,就可能去偷去搶。所以,金錢只是一種工具,怎樣運用這種工具卻可以看出一個人品性的高底,但是一個人錢多錢少並不能衡量他的品性。
很希望各位在這商品經濟的滾滾大潮中,能夠時時保持一種清醒的心態。因為人生的幸福是全方位的,是流動性很強的。人生的價值也是全方位的,我們千萬不要因小失大,以小我失去大我。一滴水只有融人大海才不會枯竭,當一個人只有把自己交給眾生,像菩薩那樣無我地為眾生服務的時候,才能煥發出無盡的生命力,才會使生命發揮出最大的價值。在我們世間法中,人們很看重自己生命的價值。菩薩卻是完全無我的,從來不看重自己生命的價值,正所謂只管耕耘,不問收穫。《金剛經》上講:如果阿羅漢說自己是阿羅漢,這個阿羅漢就已經不是阿羅漢了。就是說,當一個人已經有了很高的修行,很高的境界,取得了某種證悟的時候,他如果標榜自己,也就恰恰得出一種反證;這個人的修行境界實在還是很低的。就像阿姜查在他的書中扉頁上寫的一段話:有人問我“你可能就是阿羅漢吧?”我說:“我只是森林中的一棵樹,鳥在上面結巢,它長滿了花果,風吹來的時候,葉子在上面沙沙作響,但是樹從來不說自己是樹,樹只是樹。”多麼平實優美的語言呀,但卻體現出一種深邃的人生境界。
當今的社會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偽科學、假道學憑著先進的宣傳媒介肆意泛濫。如果我們不能夠很好地觀照自己,很可能就會迷失了自己。尤其一些號稱弘揚佛法的人,常常以弘法之名在名聞利養上、在個人利益上用功夫。有的人是披著宗教的外衣,藉以揚自己之名,擴自己之勢;也有的人雖然沒有披著宗教的外衣,但卻以世人的利益投其所好地宣揚著與佛法相悖的思想。現在我們在書攤上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書,比如這個大師出山了,那個活佛轉世了。更還有一些不能公開發行而私下裡互相傳遞的小冊子、複印件。所有這些宣傳媒介的泛濫,不但干擾了文化的正常發展,更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混亂,使人們難以把握住一種正確的知見。比我們現在更晚的下一代人其未來的趨勢更是令人憂慮。這一代人,有人稱為電視一代人,他們是靠看電視成長起來的。他們不喜歡看書,覺得書上的文字太枯燥,不如看電視更直觀,更省力,更富於刺激性。而我們有些編導為了投其所好,更使用了一些很庸俗甚至很低級的手法來取悅觀眾,挑逗觀眾。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是文以載道,是以文化傳播這種手段使人明理,使人凈化,使人養成一種良好的道德,以便自覺地擔當起社會的責任。但是現代的文化傳播,許多東西是混淆的,使人茫然,便人迷失,或者使人見多不怪以至麻木不仁了。
我講《金剛經》的觀般若,就是希望大家在現實生活中,要用般若這把寶劍來護持自己,安身立命。不管是對待生活,對待知識,還是對待自己的修道,都要運用智慧。這種智慧不是我們自以為是的聰明才智,而是佛法的大智慧。或許有人會疑問:我現在還不信佛呢,為什麼要讓我以佛法的智慧來作為標準?這隻是一種建議,無論我們信佛與否,很希望我們都能以一種包容的心量、一種平和的心態先來好好看看佛法的道理,然後再得出你的結論。
實相般若本來不應該用語言文字來講。實相般若是法界、真如以及開悟以後的本來面目。法界、真如以及涅槃,所有這一切又都稱為實相實相的究竟是什麼?《金剛經》是這樣講的:實相無相。為什麼這樣講呢?釋迦牟尼佛兩千五百年前在菩提樹下悟道時,證到了三大定律。對這三大定律,我們可以用生活實踐加以印證。釋迦牟尼佛證到的第一個規律是:一切生命現象都在生老病死當中。就是說小到微生物,大到我們人類,都不離生老病死這個規律。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這個規律,就是要讓我們正確地認識和掌握這種規律,從而更好地安身立命。第二個規律是:一切精神現象都在生住異滅當中。生,就是念頭產生了;住,就是念念相續,相對穩定的狀態;異,就是遷流變化;滅,就是消失了。第三個規律是:一切物質現象都在成住壞空當中。成,就是生成了;住,就是相對穩定;壞,就是緣散了;空,就消失了。
首先,我講一講我們的生命現象。在生命現象中,我著重講一講我們的精神現象。在《金剛經》上講到我們的精神世界時是這樣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在禪宗史上,很多人因為這三句話而覺悟,也有很多人死在了這三句話上。我們的心念念相續,如果用心理學來給大家描述,我們的心有成像的能力,每一次成像就像電影膠片中的一個分解鏡頭,每一種成像的連續,就產生了想,想所產生的對事物的分別、判斷就是思,思與想連接起來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實際上思想最小的單位是念,當念念相續的時候,就形成了思想。思想在佛法是用意識來表示。我們的意識像河流一樣川流不息,泥沙俱下,因此稱為意識之流。因為我們沒有修定的功夫,沒有經過修行和證悟,所以就發現不了自己的心。當我們修定打坐時,就會發現沒有一種影像會固定在大腦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做主把握住自己的心。如果找們不能夠把握住自己的心,也就不可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修道的過程,就是為了調整我們的心,使我們的心產生恆定力,更大程度地煥發出它本有的光明。
禪宗在唐代發展到頂峰的時候,有很多的禪宗大德刺舌頭或身上的血與金粉混合在一起,用來書寫《金剛經》。也就是說,當時在禪宗修學《金剛經》已經形成一種熱潮。在四川有一位大師叫馬金剛,因為他講《金剛經》,寫《金剛經》書鈔,對《金剛經》很有研究,在當時的佛教界非常有名望,所以被稱為馬金剛。當時在江西和湖南一帶,禪宗非常盛行,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及禪者。馬金剛就把自己寫的《金剛經》書鈔擔了一擔,跋涉千山萬水,要去找一個人來印證一下。當他走到湖南境內時,遇到了南嶽門下的一位老太婆在路邊搭了一個茅屋賣點心。馬金剛走了一路又飢又渴,就想討些點心吃。於是,他就對老太婆說:“老人家能不能給我一些點心吃?”老太婆就問他:“你擔的是什麼呀?”馬金剛說:“我擔的是《金剛經》書鈔。”老太婆說;“《金剛經》上有句話我想請問你,如果你答出來了,我就給你點心吃;如果你答不出來,我就不給你點心吃。”他心想:問到我頭上來了,《金剛經》裡面的內容我哪一個不知道呢?於是,他就請老太婆隨便問。老太婆說:“《金剛經》上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請問你要點的什麼心呀?”這位馬金剛當下愣在那裡,不知如何對答。於是,點心沒吃成,倒使馬金剛回去之後好好地反照自己,使他在後來又更上了一層樓。這時,他就把以前寫的《金剛經》書鈔全部都燒掉了。
從文字上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種意識之流,本無所謂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們人的每一個心念當下就具足萬千個法界。當我們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時,為了方便,在方位上我們分東南西北,在時間上我們分一天為二十四個小時,其實無論是方位還是時間的區分,都是我們人類所安立的假名。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同樣是這樣的假設。其目的是為了建立人類的歷史,便於我們對某種事物的表達。但如果從真如法界上來講,本無所謂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就是現在,就是未來;現在就是過去、未來;未來就是過去、現在,這三者是相融的,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過去的已經過去,現在的正在遷流變化,未來的還沒有到來,而我們一般人的心卻在這之中患得患失。
禪宗所謂的十地頓超,就是要讓我們透過語言文字深入到般若的實相當中去。人生的本質就是實相無相,但是凡夫不能用緣起的觀點悟到實相性空,因為悟不到實相性空,所以就執著於事物的形象。比如認為這個房子是實在的,而不去想這個房子是由磚瓦石塊聚集而成的,它將來必然是要消失的租借;即便它現在存在,它的當下也是性空的。正如《心經》上所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有些有智慧的人,當他看到別人死亡時,可能會悟到:人生不過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去,註定是一場空。可是他沒有進一步想,我們生命的當下其實就是空的。因為我們的生命每時每刻都在生滅變化著,沒有一刻是固定不變,是實實在在的。我們可以用認識的方法來辨別一下,生命如果沒有每時每刻的生滅變化,怎麼會導致最終的死亡呢?
《金剛經》上講,我相是虛妄的,沒有一個實在的我相。但是我們一般人往往執著於我相,執著名是我的,利是我的,房屋是我的。其實有哪一種東西真正是你的呢?當死亡來臨時,你被迫放下一切。與其死的時候你被迫得放下一切,還不如在你活著的時候就看破生死,早早地就放下對自我的執著。看破了生死,就打破了小我,就可以進入到菩薩無我的境地。我們凡夫之所以有很多煩惱,就在於有我。老子說:“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如若無身,何患有之?”這話聽起來似乎有些偏頗,但是當我們不以人為本位地看待生態,看待社會的時候,也就釋然了。當我們以自我或以擴大了的自我(集團的形式)為本位的時候,矛盾就來了,煩惱也就產生了。
當社會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現狀,能明白無我的道理已經很難,若能按照這樣的道理去做就更難。因為我們畢竟都是社會人,都是在這個社會的熏染下成長起來的,要想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認識,改變我們的行為,就猶如脫胎換骨,必然會是很艱難,很痛苦的。比如在學佛的初期:當有人無端地污辱你的時候,你的理智就會告誡你要忍耐,你需要用很強的理智才能壓下去原有的嗔恨心、我慢心。這種對自我控制性的約束的確是很痛苦的。痛苦的根就在於我執,因為執我為實,被別人污辱時才會感到很痛苦;當理智明白了我執是錯,想強行斷除我執時,就像忍痛割愛,內心裡會產生強烈地碰撞,就愈發感到痛苦。在佛法里,把這種明白了佛法的道理,不能忍卻生要忍,叫做生忍。即難忍能忍,咬緊牙關也要忍。還有一種是法忍,就是領會佛法之後,按照佛法的道理慢慢地消磨自己的習氣。另外就是無生法忍。這是菩薩的境界。菩薩因為甚深的禪定功夫,以眾生之身為己之身,人我不二,具有一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他以度化眾生為己任,度化眾生而不以為度。所以,他連忍的念頭都沒有,這就是無生法忍。
我們每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在方方面面都有可能與人發生衝突。我時常問別人:“在我們漢字中,哪個字的頻率出現最高呢?”就是這個“我”字。我現在在這裡講話,如果我不說“我”字,好像話都講不下去了。當我講到“我”時,就把我和大家對立了,這就把能所分開了,我是能講,你們是能聽。從語言文字的假名安立上來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從境界上來說,千萬不要有能所之分,而要能所兩忘,參禪打坐要能所兩忘,為人處事也要儘可能地能所兩忘。我為什麼要說儘可能呢?因為要想把佛法的道理落實到生活的實處是非常艱難的。我們人的惰性、習性是非常頑固的,我們社會的現實是非常嚴峻的,如果沒有智慧的明燈為指引的話,是很可能半途而廢的。所以,當我們面對自身及現實的種種狀況,唯有以佛法的智慧為觀照,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住自己。
佛法講實相無相,但我現在講無相的時候,又有很大的顧慮。顧慮什麼呢?因為很多人認為佛法是消極厭世的,其原因就在於佛教在歷史上張揚了空,而忽略了妙有;重視了對體的證悟,而忽略了用和相。人們之所以認為佛教是消極厭世的,就是因為佛教所張揚的空的概念給人們的印象太強烈了,這就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反差太大了。
昨天,日本留學僧木村法師講的公案就很能說明問題。他先講了一個執著空的例子,比如有人說這個杯子是由各種條件組成的,它的自性是空的;又說我們的生命是由四大五蘊組合而成的,自性也是空的。當這個人偏執於空的時候,你就拿這個“空”的杯子去敲他“空”的頭,看他疼不疼?如果他說疼,那就不是真空。另外,他還講了一個執著有的例子,比如一個人潛到海底,發現一個寶貝,可是拿又拿不動,於是他就用手牢牢地抓住不鬆手。在這種時候,你不要去同他講道理,還是去敲他的頭,當他頭疼時,他就不得不鬆手趕緊去捂頭。顧此失彼,這就是人執著於有的特性。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對佛法的真空妙有能有一種整體的認識,既要明白當體的性空,又要懂得用和相的妙有。只有這樣,面對這有形的琳琅滿目的世界,我們才能既不執迷,又不落於頑空。在做事情的時候,我們才能但看腳下,莫問前程,而行於中道。
為什麼現在的社會精神失常、心理不健康的人很多?原因就在於我們現在的社會太過分地張揚了以人為本位的物質生活,使人眼花繚亂地招架於有形的物質供界,而心卻是迷惑的、迷亂的。我們如果不懂得空的道理,對空視而不見,不去考慮生死的問題,一味地耽於聲色之中,必然導致內心的空虛和墮落。以人的習性而言,人用理性去生活肯定比用感官去生活要艱難得多。但是人要想真正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使心澄凈、自在,就必須要靠理智。理智的核心就是佛所親證的般若智慧。
生活禪夏令營是一種方便,通過這個方便之門,我們可以走進佛法智慧的大海。我希望大家在修學生活禪的時候,要儘可能地以戒定慧的道理去實踐、去證悟,最終的目的是理事合一。所以臨濟義玄講:“離相離名人不稟。”也就是說,人的心是善於攀緣於名和相的,離開了名相,我們的心就無處著落了。
在《金剛經》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這段經文:“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佛的意思是這樣的:在座的各位比丘,你們應該明白,我講經說法是治病良葯,我以我的觀照知道你們有這種病,我才給你們吃這種葯。這種葯的葯量要恰到好處,葯量太大了,就會成為毒葯;葯量太小了,就不能把病連根拔除。因此,適時適度地談論信仰,如理如實地理解佛法,不要過度,也不要欠量,這很重要。如果你對一個獨善根性的人講大乘佛法,他的心力不能夠承受,就像焦渴的小花小草,面對瓢潑的大雨,只會把它們連根摧毀,而沒有任何益處。比如對一些專念阿彌陀佛的老頭、老太,當他們問你西方世界有沒有時,你就應該直言說有。如果你不是這樣直接回答,而是給他們灌輸一些深奧的思想內涵時,你就是害了他們,就像以一把無名的刀子斬斷了他們的法身慧命。因為以他們的能力和有限的生命時間,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入地理解更多的佛學思想了,所以,你讓他們只管一心念佛,對他們就是最當機的法門。因為他們念一句佛號,就能一念清凈,一門心思念下去,他們就會念念清凈,得到真實的受用。當你把所有問題都擺在他們面前時,你就等於給他們設置了很多的障礙,使他們陷於迷茫和困惑。
釋迦牟尼佛是一位很偉大的教育家,他在教育人的時候因人而異,具有很多不同的方便法門。比如說生活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非常貪婪。因此《金剛經》上就有十度的法門,第一度就是布施。財布施,在別人生活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給予財物的幫助;在別人感到恐懼,或生命受到危害的時候,我們應該挺身而出,給予無畏的布施;還有一種是法布施,在所有的布施當中,法布施最為重要。因為通過使人明白道理這種布施,對人的幫助最為根本。這三種布施之間又有內在的聯繫。另外,我們在行布施時要三輪體空,就像我現在給大家講《金剛經》的時候,我不能有我的形象,不能有講法的形象,也不能把你們看成一種被動的、機械的承受,也就是把能所和物都要空掉。因為一切貪戀功德的心(有貪就會有失),總是要落在一種相對的境況之中。我們要想超越這種相對的境況,就要打破這種相對的東西。我們世間的學問有很大的成分就是由相對而產生的,因此它是很有局限性的。唯有佛法是超越這種相對的,所以我們說佛法無邊。
在佛法的十度當中,我只舉例說明布施這一度,其它的九度希望大家能夠舉一反三。其它九度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願、力、智。如果我們要想完善自己的人格,從這十個法門中任何一門深入進去都是可行的。如果我們能以這其中任何一個法門作為人生的指南,也就不會覺得做人難了。我們平常之所以覺得做人難,就是由於無論我們做什麼,總是想做給別人看,我們如果不空掉自己,就是百般修飾,也超不出小我的框框,於是,便總有不如意的感覺。
《金剛經》的思想內涵非常深厚,我用兩個小時來講,只能講些啟示性的東西,起一種導讀的作用。其目的是想引導大家走進《金剛經》,受持讀誦《金剛經》,並用這一根本的經典來生髮我們本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