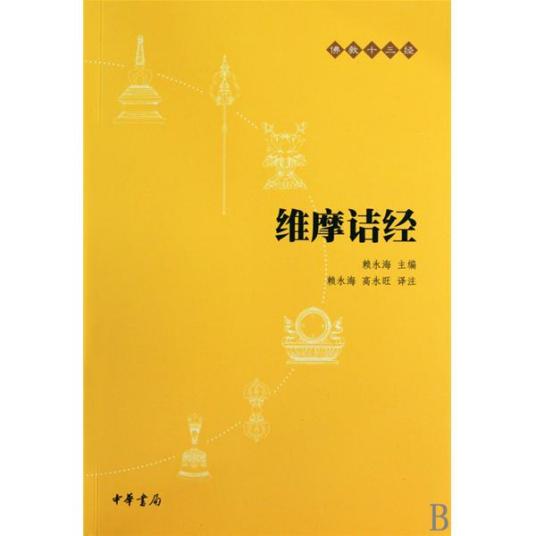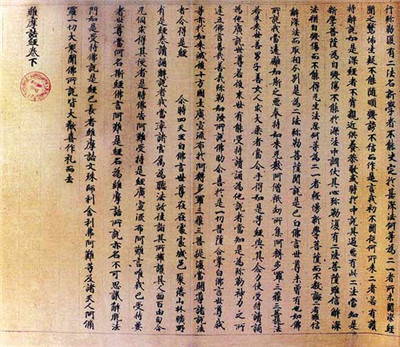慧能,生於公元638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圓寂於公元731年(唐玄宗先於十九年)。他俗姓盧,出身破落官僚家庭,家境比較貧苦,曾以賣柴為生。後來投靠寺院,為行者,在寺院從事打柴、推磨等勞動。由於他對佛教義理很有領悟,得到了禪宗第五祖弘忍的賞識,傳給他衣缽,後來成了禪宗第六祖。慧能所創造的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它不追求煩瑣的宗教儀式,不講累世修行和布施財物,不主張念經拜佛,不研究經典,甚至不講坐禪,主張專靠精神的領悟把握佛教義理,總之,提倡“頓悟”。本文首先從慧能思想形成之背景來探討《壇經》與《維摩詰經》的相關性。
據《壇經》,慧能生涯可分為三期:一是出家之前;二是從弘忍門下到隱居生活;三是從受戒到圓寂。其中二是慧能大乘頓悟不二法門思想形成時期,三是他宣揚“大乘頓悟不二法門”思想時期。
慧能在弘忍會上住了8個月,在《壇經·三》中記載:慧能於碓房,踏碓八個余月。
但是,他離開弘忍後,16年(或者5年)時間在哪兒隱居生活,各家說法不同。例如,王維撰《六祖能禪師碑銘》說:禪師逐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凈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
又,柳宗元撰《賜謚大鑒禪師碑》說:(慧能)遁隱南海上,人無聞名。又十六年,度其可行。
又,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記載:某甲後至曹溪,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
據敦煌本《壇經》,慧能講法的時候,引用過兩部經典經文,是《維摩詰經》和《菩薩戒經》。他不懂文字,只能憑聽經文來理解道理,在《壇經·八、四二》中記載:(慧能)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即識大意。……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到,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佛意,便與法達說《法華經》。
而且他明心開慧,都是聽到別人誦經或講話而得到的。在《壇經》記載: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五祖夜至三更,喚慧能堂內,說《金剛經》。慧能一聞,言下便悟。
這就是說,慧能覺悟得法、接人講話時引用過的經文,是從聽別人誦經和講話而得到的。那麼,慧能在哪聽到佛法呢?筆者認為,有兩個時期,慧能聽到佛法。一是,在弘忍門下修習過程中;二是,在隱居生活中。
慧能在弘忍會上8個月修行,只在碓房天天勞動,可能沒有機會與別人學習佛經,而且沒離開過後院,在《壇經·八》慧能說:我此踏碓八個余月,未至堂前。
但是,他在後院,聽到別人誦經的可能性很大。因為,他住的地方是剛入門修行而還沒受戒(沙彌戒或比丘戒)的人,即行者們的住處。他們的主要功課之一是誦經,特別沙彌階段的人著重於誦經來修行,因此他們基本上整天誦來誦去。這樣環境,肯定給不識文字的慧能提醒了很多佛教教理,所以,他作呈心偈而覺悟受法的機會,是從一位沙彌誦經(即神秀的呈心偈)而得到的。在《壇經·八》記載:
有一童,於碓房邊過,唱頌此偈。慧能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言:“適來誦者是何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大事,欲傳於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稟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無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離。”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個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佛地。”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另外,16年隱居生活中,慧能與農民、商人或獵人等俗人在一起,隱居期間之行跡,可惜,基本上沒有有關資料。
在上文中已經提過行者的主要修行方法是誦經。那麼,他們念什麼經典呢?在《頓悟大乘正理決·摩訶衍的第三道表疏》里,摩訶衍認為:現令弟子沙彌,未能修禪,已教誦得《楞伽》一部,《維摩》一部,每日長誦。
在【法】戴密微著《吐蕃僧諍記·史料疏義》記載:“摩訶衍和尚大約是在787年788年間離開敦煌的,在論戰以前,他在吐蕃就已經居住了三、四年的光陰了。”按照此見,摩訶衍是大約在八世紀末的一名禪師,非常接近慧能生活時期。按照這句話,可以推想到:當時,禪宗剛出家修行的沙彌們,在日常生活中都念《維摩詰經》。無論慧能聽過多少經典,然而他畢竟在講話中只引用了《維摩詰經》和《菩薩戒經》:《維摩詰經》是七處;《菩薩戒經》是二處。這表明《維摩詰經》是慧能最喜歡的佛教經典。因為,一般來說,一個人在談話中提出的思想和自己心中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還有在《壇經》中他提到《維摩經》和《凈名經》的兩個經名(《凈名經》與《維摩經》是異名同經)。一般誦經時,要把一部經從頭到尾連續念出來。如果慧能只有聽到別人念經,他就不會知道《維摩詰經》的兩個經名。也就是說,慧能有可能聽過《維摩詰經》的講解。
另外,《菩薩戒經》也是慧能思想形成的主要來源之一。《壇經》的經名也是從《菩薩戒經》的菩薩戒(無相戒)精神而來的。大乘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序》記載:是時刺史韶牧等,請六祖於大梵戒壇,受(授)無相戒,說摩訶頓法。門人錄其語要,命曰《壇經》。
慧能為什麼單單重視《維摩詰經》和《菩薩戒經》呢?經分析,這主要是和慧能的長期居士生活分不開。然而慧能長期的居士生活經歷卻長期未被人重視。從佛教戒律來看,慧能在法性寺受戒之前應該是居士身份。在《曹溪大師傳》雲:
儀鳳元年正月十七日,印宗與能大師剃發落。二月八日,於法性寺受戒。……能大師受戒,和尚西京總持寺智光律師,羯磨闍梨蘇州靈光寺惠靜律師,教授聞梨荊州天皇寺道應律師。後時,三師臂於能大師所學道,終於曹溪。
又,《六祖大師緣起外紀》記載: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志”八字。此石今存黃梅東禪。
佛教教團有四部大眾,即比丘(男)、比丘尼(女)、優婆塞(男)、優婆夷(女),前兩者是出家僧眾,後兩者是在家信徒,即居士。慧能在弘忍門下時的稱呼是“盧行者”,他從出家進入寺院後到受戒之前的階段是行者身份。對出家男性來講,受戒有兩種,即沙彌戒和比丘戒。出家之後,如果受戒時不到成人年齡的話,先受沙彌戒(這受戒人不算完整的僧人),到了成人再受比丘戒。如果已經成人的話,直接受比丘戒。慧能出家時已經到成人年齡。關於他出家年齡的記載有《曹溪大師傳》:
至咸亨五年,大師春秋三十有四(七)……大師其年正月三日,發韶州往東山。…大師出家開法受戒,年登四十。
在法海等撰《六祖大師緣起外紀》中記載:年二十有四,聞經有省,往黃梅參禮。
在劉禹錫撰《大鑒禪師碑》記載:大鑒生新州,三十齣家。等等。如果他在弘忍門下受戒的話,應該能受比丘戒。但是,據以上材料,可知慧能在覺悟受法時期,和隱居生活的十六年期間,只是一位與維摩詰一樣的居士。
“慧能”這個名字又是從哪兒來的?這是俗名還是法名?這在《壇經》中沒提到過。不過在《六祖大師緣起外紀》有有關的記載:
有二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濟眾生;‘能’者,能作佛事”。
按照上文,“慧能”應該是俗名,出家之前六祖的姓名是盧慧能。按照佛教的一般常規,師父給弟子傳法時或者剃發受戒時,應當為弟子取個“法名”。如果在受法時或者受戒時,慧能得過“法名”的話,在《壇經》或者《曹溪大師傳》等里,應該是有記載的。但是,現存可據資料上沒有這些內容。因此,慧能就是六祖的俗名。後來禪宗的一位大師,即慧能的法孫馬祖道一,也是用他的姓“馬”來作為他的法號。
那麼,我們又怎麼理解弘忍傳給慧能“衣”呢?“衣”是指“袈裟”,是比丘受比丘戒後,才能穿的“大衣”。按戒律,居士不能用袈裟。據上而結論,可知弘忍未給慧能授過比丘戒,那麼,為什麼弘忍傳給他袈裟呢?對這問題,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雖然從佛教威儀形式的戒律來看,以居士身份,不能受袈裟;但是,從“以心傳心”的禪宗說法來看,這是正常的。因為,禪宗認為,佛教是以“解脫”為本的,慧能雖還沒受戒,但既已覺悟解脫,也能受袈裟,也可以稱他是“解脫宗師”。這種精神已經超脫“僧、俗”為二的觀念,體現了“世間與出世間不二”的“不二”境界。由於有此經歷,慧能傳法時,也特別強調“心戒”,即“無相戒”,超越“僧、俗”為二的形式差別。他主張佛教根本精神是要“當地頓悟成佛”,而不是形式上的戒律,也不是拜佛、誦經、坐禪等宗教儀式。慧能把這種執著於形式的人稱為“小根人”。
慧能十六年的隱居生活不是普通修行人那樣自願自作的,在《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里,慧能自說:某甲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命似懸絲”是指生命就像懸絲一樣隨時都有危險。“命似懸絲”的生活對慧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是應該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的。慧能在16年裡一直過著“命似懸絲”的生活,所以他一定經常體驗“當面生死”之境,由而深刻體會到“一行三昧”修行的重要性。所以慧能在大梵寺初開說法時,就提倡“定慧體一不二”的修行方法,即“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慧能把“直心”解釋說:《凈名經》雲:‘直心是道場,直心是凈土’。
慧能認為,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直心”之境,一旦能達到這種境界,這就可以說是“當處凈土”、“當處道場”。
筆者認為,在《壇經》中表現出來的慧能思想,基本上都是從這些居士生活經歷基礎上形成的。如果慧能沒有這些長期接觸實際生活的艱難的居士生活經歷,也許沒有如今天這種面目的《壇經》思想。如此來看,我們不難推測到後來慧能宣揚“無相戒”的僧俗不二精神。因此,要研究慧能的《壇經》思想,我們先要了解他的這些特殊背景。總之,慧能雖然通過《金剛經》發心而覺悟,但從上述的內容來看,不難看出對其思想形成影響最深的還屬《維摩詰經》。《維摩詰經》的強烈的居士佛教精神,被有長期居士生活經歷的慧能所深為理解和同情,並發揚為有著強烈的居士佛教精神的《壇經》。但是,《維摩詰經》和《壇經》在居士佛教方面的相關性,很少為人重視和指出。而指出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壇經》非常重要。
二、《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對《壇經》思想的影響在中國佛教史上,《壇經》是影響最大的禪門經典之一。一般認為,它的思想淵源於《金剛經》的般若思想或者《涅架經》的佛性思想。但是,筆者認為,《壇經》思想並非如此,而是由於《維摩詰經》之將“般若性空”和“如來種”(早期佛性思想的一種)思想融合起來,宣揚“人性本凈”、“煩惱即是菩提”的“不二法門”思想。本文把《壇經》思想分為四個方面來探討《維摩詰經》思想對《壇經》思想的影響。
人性本凈
在《壇經·十四》里,慧能解釋說: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凈名經(維摩詰經)》雲:“直心是道場,直心是凈土”,莫心行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
慧能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把精神專註於一境,這就是“一行三昧”。“一境”是指“直心”的狀態,一旦能達到這“直心”境界,就可實現清凈道場和清凈佛土。這就是符合於《維摩詰經》宣揚的“直心道場、直心凈土”思想。
在《壇經》里強調的“直心”就是《維摩詰經》中的“心凈”。“心凈”是《維摩詰經》的中心思想之一,《維摩詰經》的“不二法門”思想也是在“心凈”思想的基礎上才能成立的,如果有人還沒有“心凈”的基礎,他就不能逍遙於“煩惱即是菩提”的境界。
慧能認為,本來“佛性常清凈”,但是人有顛倒妄想,因這種顛倒妄想的分別心而執著“妄”、“凈”等差別相,因此不能“心凈”。若能體會到妄凈不二,就可證“心凈”。在《壇經·十八》中,慧能說: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凈,亦不言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凈,人性本凈,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凈。不見自性本凈,起心看凈,卻生凈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卻是妄也。這種思想完全符合於《維摩詰經·人不二法門品》中“垢凈不二”思想。如經中借德頂之口說:垢凈為二,見垢實性,則無凈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慧能從“佛性常清凈”開始,提到了很多與佛性異名同義的概念,即“直心”、“本心”、“本性”、“法身”、“真如”、“自性”、“法性”、“自心”等。但是他最注重的主張是,人人本來都具有的“人性”是常清凈的。慧能說的“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都是主張“人性”就是“佛性”。“佛性常清凈”說法是慧能的中心思想之一,這也叫“人性本凈”思想。他在《壇經》中,除了“人性本凈”以外,還提到與“佛性常清凈”同樣意思的說法,即“明鏡本清凈、性體清凈、自性本凈、本性自凈、自性清凈、世人性本自凈、自性常清凈、世人性凈”等多種說法。
慧能的呈心偈,在敦煌本、西夏語本《壇經》中記載: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
除了此兩本《壇經》以外,黃櫱希運的《宛陵錄》、《祖堂集》、永明延壽的《宗鏡錄》、惠昕本《壇經》、大乘寺本《壇經》、興聖寺本《壇經》、高麗本《壇經》、德異本《壇經》等,把“佛性常清凈”一句作為“本來無一物”。按照楊曾文先生在《“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探討》中提出的“敦煌原本是最接近《壇經》祖本的”內容。樓宇烈先生,在《讀慧海“頓悟人道要門論”隨記》中曾經說:“《壇經》中慧能呈心偈(得法偈)的後兩句由“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演變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其來源就在《宛陵錄》”。
在“佛性常清凈”說法中,慧能究竟要提倡的“人性常清凈”又落實為人之“平等直心”。而且他進一步認為,“平等直心”就是“功德”。這種“功德”是從“法性”出來的。他說: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
而且,慧能把“禪定”和“智慧”完全統一起來認為定和慧是一體的,定慧不二。在《壇經》中,提出了達到“不二法門”境界的方法,即“一行三昧”說。這就是在“定慧體一不二”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直心是道場”,“直心是凈土”的“不二法門”境界。他還認為,大乘菩薩精神的“上求菩提”和“下化眾生”是分不開的,“上求菩提”的修行,就是“下化眾生”的菩薩行。
慧能之“心凈”落實於人之“直心”,落實於“定慧不二”之心,落實於“菩提慈悲不二”之心,他還進一步落實為世間與出世間不二之心。而後者就是他的心中求佛思想。
心中求佛
在《壇經·三五》中,慧能很明確地闡明無論是此岸或彼岸,若證得凈心,就能達到真正解脫的境界。慧能說: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凈其心,佛言:“隨其心凈則佛土凈”。這就是說,咖果有人要解脫,先使自己心成為很乾淨的狀態是必要條件。這里說的乾淨不意味著垢對凈的乾淨,而是指無分別的直心本凈。慧能說:但行直心,到如彈指。……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
在《壇經》中可看出慧能思想是,凈土和污土、眾生和佛這樣的相對觀念,都是從自己“本心”中產生出來的,這個“本心”不能離開現實環境而存在,於是事物的垢凈也在於“自心”中,如果自心清凈,這就是成佛。但是,有人想要清凈,然而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自心是本來清凈的,再要清凈這樣的心就是煩惱而已。所以,慧能很明確地批評說:不見自性本凈,起心看凈,卻生凈妄。世人性本自凈,萬法在自性。
慧能認為,佛是從自己心中作出來的,如果沒有自己的本性,也就沒有要解脫的佛性,佛性即是人性,人性即是佛性,因此,不要從外邊追求覺悟。
總之,慧能,首先提倡“涅架佛性”說的“佛性常清凈”。其次把《維摩詰經》“直心是凈土、直心是道場”的“直心”和“隨其心凈則佛土凈”的“心凈”說法統一起來,說明“心、物”不二思想說明心中成就佛土的思想。
慧能又認為,要向心中求佛,不要執著於向出世間求佛,不要執著於向外求歸依。慧能很強調“破除執著於形象”而“頓悟一切皆空的真理”。慧能不重視佛教傳統的戒律,而特別重視大乘菩薩精神的“無相戒”。可以說,“無相戒”是慧能的佛教戒律。在《壇經·一》中記載: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刺史韋琚,及諸官僚三十餘人,儒士三十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這里他給聽眾傳授“無相戒”和講解“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不管是出家僧人和還是在家居士,也不管是否佛教徒,都能受這“無相戒”。這說明“無相戒”已經超越了佛教宗教儀式的一般形式。而且,慧能的戒法已經超越了“僧、俗”等相對觀念在形式上的“是非分別”。他把《維摩詰經》的“世間與出世間不二”思想繼承並加以發展,得出了“僧、俗”不二的看法,也就是說不要執著於僧俗差別,不要執著於一定向出世間去求解脫,不要執著於在出世間中成佛。
在《壇經》中,慧能傳授了四個方面的“無相法門”。即“無相自歸依三身佛”、“無相發四弘大願”、“無相懺悔”、“無相自歸依”。
首先,慧能闡明自己的“無相自歸依三身佛”思想。三身佛是指化身、報身、法身。按佛教傳統說法來講:化身是為了普度眾生而顯現出來佛身;報身是長時間修行萬行而成就的佛身,也可以說,具三十二相的庄嚴佛身;法身是本來清凈的佛身。而慧能對“三身佛”的看法則不同。慧能認為“人性本清凈”是法身,“自性變化”是化身,自性“念善”是報身。因此,慧能說: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
在《壇經·二三》中,慧能傳授“無相自歸依三寶戒”說: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凈眾中尊。
慧能解釋說: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凈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尊。自心歸正,念念無邪故,即無愛著,以無愛著,名離欲尊。自心歸凈,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眾中尊。
慧能最後按照佛經,證明他的“無相”法門觀點:經中只即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
在《壇經》中,慧能提到《金剛經》的重要性,認為“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人般若三昧”。在《壇經·二八》里,慧能說: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
這里,慧能主要重視《金剛經》破相,特別是文字相,證平等境界的思想。在《壇經·四三》里,就用《金剛經》這種破相不假文字的思想來解釋四乘法義,他說:汝向自身見,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不唯四乘,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無雜,且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
這意思是,修行大乘法門的人,按照《金剛經》的道理,自心覺悟自性。人自己使用自己的智慧,觀照自己本性中已經存在的“般若之智”,不要執著於經文的文字。如果有人只誦經而執著於文字的話,這就是“小乘”。只了解經文的道理而不修,這就是“中乘”。雖然理解道理而依法修行,但是不超越“我空、法空”的觀念,這就是“大乘”。萬法、萬行都無所不通,雖然已經清凈無雜,而不離開一切法相,這就是“最上乘”。這樣,慧能認為求三乘法,都是不究竟的。只有自心覺悟自性,不著一切相,才是真正的求佛乘,才是最上乘。這也是講向內心求佛的道理。
慧能在《壇經·三五》中說: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
這就是說,這種“悟”和“迷”就是佛性的覺悟不覺悟。“自性”指個人的心,也叫“自心”。在慧能看來,“佛”不在遙遠的彼岸世、界,而在於個人的心中。“自心”不覺悟,即使是整天念經、拜佛、坐禪、營造佛寺,也不過是凡夫而已。慧能把成佛的途徑,全部轉移到對自己“本性”的覺悟上來,提倡內求於心,這就是他的“頓悟成佛”的出發點。
頓悟成佛
《壇經》的根本宗旨是闡明“頓悟法門”。在《壇經》中,最多提到的也是“頓悟法門”。在《壇經》里,與“頓悟成佛”有關的說法有:
“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頓悟菩提”、“本性頓悟”、“一悟即知佛”、“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但行直心,到如彈指”、“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悟則剎那間”、“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自性頓修”、“言下大悟”、“見性剎那即是真”、“悟即眼前見世尊”、“自心頓現真如本性”、“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一念智即般若生”、“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後念悟即佛”、“一時皆現”、“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一聞言下便悟”、“言下心開”。
慧能的這種“頓悟”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當時佛教流行的“看心看凈”的修行方法提出來的。慧能在《壇經·一八》中很明確的指出“看心看凈,卻是障道因緣”。到了隋唐時代,佛教已經成立了很多宗派,即天台宗、華嚴宗、凈土宗、慈恩宗等等。它們基本上都提倡“漸修”法門。其中,神秀是弘忍門下的禪師,是慧能的師兄。他的主要禪法也是“看心看凈”的漸修成佛法門。從《壇經》看,慧能特別強調“頓悟”法門的直接原因則可能是針對神秀的“看心看凈”的禪法。
在《壇經·一九》里,慧能說: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本性自凈自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雲:‘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慧能以一種獨特的觀點來解釋“坐禪”和“禪定”。首先也說明什麼是“坐”、“禪”,他認為對外境無念是名為“坐”,在本性不亂是名為“禪”,這是指“外坐內禪”。其次,他解釋什麼是“禪”、“定”,他認為對外境沒有分別相是名為“禪”,在內心不亂是名為“定”,這是指“外禪內定”。從事實來看,“禪”都有“內”、“外”,但是,“坐”是只有“外”,“定”也是只有“內”。因此,在“禪、定、坐”中的核心概念是“禪”。“禪”統一了“外坐”和“內定”,把“外身”和“內心”完全統一起來。這樣慧能就否定了宗教儀式的根據,也否定了打坐修禪的根據,也否定了漸修的根據,而主張“頓悟成佛”思想。慧能這種禪法完全符合於“定慧體一不二”的“不二法門”思想。
在《壇經·十三》里,慧能說:定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又,《壇經·十七》中說: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經雲:“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這就完全否定了“定慧為二”說法。佛教傳統說法是“先定後慧”,即首先達到斷絕見聞覺知的人定狀態,然後發出來真正的智慧。這種說法與“離開煩惱而得到涅架”的思想是一脈相通的。而慧能認為,“定”和“慧”不能分開而說的,它們是精神的兩面。“定”是“慧”的本體,“慧”是“定”的作用。自性雖然有“見聞覺知”的意識活動,但是沒受到萬境的污染,而自由自在。這就是《維摩詰經·佛國品》宣揚的“自性,對於外境能好分別一切法相,而內於真空上如如不動”的“內外不二”思想。慧能的“定慧體一不二”思想,特別對“臨濟禪”有相當深刻的影響。臨濟宗的“參話頭”方法是不離意識而保持無雜念的禪定狀態,這就是玄覺在《證道歌》中所說的“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追求“平常心是道”的境界。
這種思想還根據於《維摩詰經·弟子品》中,維摩詰批評舍利弗說: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
這把“道法”和“凡夫事”、“煩惱”和“涅槃”統一起來。這種思想,慧能也繼承了,並發展為“即煩惱是菩提、變三毒為戒定慧”不二法門思想。慧能又強調“心不住法即通流”時,引用了《維摩詰經》里“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的一句話。
在《壇經·三o》里,慧能闡明“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時,又引用過《維摩詰經》的“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說法,他說:不悟即是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菩薩戒經》雲:‘(我)本元自性清凈’。識心見性,自成佛道。《維摩詰經》雲:‘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即時豁然”是指“頓悟”,“還得本心”是指“得契本性”。“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就是“頓現真如本性”的意思。“即時豁然,還得本心”這句話出於《維摩詰經·弟子品》,其原文為:我(富樓那)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這里,維摩詰認為,要“先當人定觀此人心,”確定此人有大根器,然後才能使大根器者“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因為能了解他人的根源或者“根之利鈍”,才能正確地引導他人,因而他人立即豁然開悟而恢複本心。在《注維摩詰經·弟子品》里,僧肇解釋“先當人定觀此人心”說:大乘自法身以上,得無礙真心,心智寂然,未嘗不定,以心常定,故能萬事普照,不假推求,然後知也。小乘心有限礙,又不能常定。凡所觀察,在定則見,出定不見。
按照僧肇的說法,這種有大根器的人,即自法身以上的大乘菩薩,雖在日常生活中,但“心常定”。這與慧能宣揚的“定慧體一不二”思想完全是一樣的。慧能也繼承這種“上根之人”之“心常定”思想,宣揚“上根人”“頓悟成佛”的思想。而且慧能提出“迷是眾生,覺悟是佛”的理論,進一步發揮“上根人”的理論。在《壇經·三o》里,慧能說:愚為小人,智為大人,迷人問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彼愚者悟解心解。迷人若悟解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
慧能用“迷、悟”來說明“眾生、佛”的區別。在《維摩詰經》里,“大乘心、小乘心”的根器差異根據是是否已經“殖眾德本”,這要求長時間的積累眾德。但是,慧能把長時間的“殖眾德本”,發展成為“一念之間”,這就完全取消了人們解脫根器上的區別。慧能的這種思想是繼承又發展了《維摩詰經》的頓悟思想。
不二法門
筆者認為,“不二”思想是慧能的核心法門。因為,按照《壇經》的內容,慧能講法時,大體上都是以“不二”法門作為中心思想。從具體思想來講,《壇經》法門可分為“定慧不二、一行三昧、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坐禪(禪定)、無相戒、摩訶般若波羅蜜(最上乘)、頓悟成佛、佛性常清凈·人體本凈、般若三昧、唯心凈土、世間與出世間不二、三科三十六對”等思想。其中,最關鍵的思想又可概括為“人性本凈”、“心中求佛”、“頓悟成佛”、“不二法門”等。這前三點上文已有述論,其實,這三點也都可看成廣義的不二法門精神的體現和表現。“人性本凈”之“凈”最終必須表現為:使心在任何一組二元相對的差別相上,不執著,不分別,體征“不二”之實相。“心中求佛”也落實在:在心證得“不二”之世界實相時,世俗之土變成佛土,世俗之人變成佛。“頓悟成佛”思想是“不二精神”在修證方法上的體現。徹底的不二精神要求在修證領域,不能有定慧的分別相,不能有修行階次地位的分別相,也不能有決定不變的大小根器的分別相,如果在修證時不著這些二元的分別相,也就是不二修證法門,這不二修證法門也就是頓悟法門。本段將要論述“不二法門”在其他領域中的體現,即“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僧俗不二”、“三十六對不二”等思想。
無念為宗說
慧能宣揚“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說時,首先從“佛性常清凈”思想來說明“無念、無相、無住”的意思。其實,還進一步解釋“無念”的內容。但是,慧能的“無念”、“無相”、“無住”最終還必須從“不二法門”來闡明本思想的真面目。而一般僅從般若性空思想來闡發此“三元”是不完全的。在《壇經·十七》里,慧能說: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何名為相?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為人本性。……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但離一切相,是無相,但能離相,性體清凈,此是以無相為體。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
在這里,慧能首先說明是以“相而離相、念而不念”的“無相、無念”作為“無住者為人本性”的基礎思想。其次,還解釋“人性本凈”是指“念念無住、離一切相、於一切境上不染”的境界。
慧能還進一步闡明“無念”說: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
這里,慧能把常清凈之佛性真如作為“念之體”。這兒,“念”這一活動,被統一於真如,被看成是“真如”這一體之“用”。因此,念之能所差別就沒有,這已經為通向不二法門鋪平了道路。“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這一句話,對後來禪宗影響頗大。慧能的呈心偈中的“佛性常清凈”後被改作為“本來無一物”,這句話對臨濟宗“看話禪”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慧能最後,從“不二法門”說法來闡明本段思想的真面目: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
《維摩經》雲:“(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
慧能認為,在日常生活當中,雖然有“見聞覺知”等活動,但是心能不執著於一切現象而自在。這里引用的“(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思想,就與《維摩詰經》別處的“不斷煩惱而入涅架”說法一樣,都體現了《維摩詰經》不二法門精神。
慧能提倡的“四乘法”中“最上乘”法是指“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慧能首先從“一念”說法來說明“般若”,然後用“即煩惱是菩提”、“定慧等”、“變三毒為戒定慧”的“不二法門”思想來闡明“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慧能解釋“般若三昧”時,首先提出“若識本心,即是解脫”,並指出“解脫”就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也是“無念”。其次,宣揚這“無念”是“於六塵中,不離不染”的“不二法門”境界。他最後指明這不二法門是“悟無念頓法者,至佛位地”的“無念頓悟”法門。
僧俗不二
慧能宣揚的“不二”思想最突出的表現之一是把《維摩詰經》的“世間與出世間不二”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僧、俗不二”。
宗教在印度和中國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不同。印度的宗教和中國相比,受政治的影響不多。而中國的佛教,基本上都是在國家統治管理下發展起來的。每時代統治者是否重視佛教,與當時佛教興衰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從歷史上看,中國禪宗的發展也是與當時執政身份的士大夫密切關聯著,他們往往以在家的居士身份,與禪師們交往。因此,中國的居士佛教就相當發達,山林佛教也因之帶有強烈的居士化佛教精神。中國佛教這種濃厚的居士佛教精神來自何處?最大的來源之一,可能是來自《維摩詰經》的主人翁“維摩詰”大居士。
小乘聲聞與大乘菩薩,同樣修“空觀”,然而卻大異其趣。小乘人只證得“我空”,而“厭怖生死,欣樂涅架”;大乘行者,不僅證得“我空”,還證得“法空”,所以能“不厭生死、不樂涅架”。大乘禪不僅認為生死和涅檠不二,還認為動靜不二。大乘禪觀的特點,不偏重於靜坐,而在於活潑的修定,不論行住坐卧,或是語默動靜,無不可修行人定。這就是維摩詰批評舍利弗在林中宴坐(靜坐)之所以,因為在維摩詰心中的禪觀是: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粲,是為宴坐;這樣維摩詰實際上已經初步提出了僧俗不二的道理。慧能則把它進一步發展。慧能把大乘佛教講的“一切皆空”,歸之為心中一切相空,把空觀引向內心的世界,在此基礎上提出“自性真空”說。慧能的所謂佛在心中,不是說佛性作為一種實體住在心中,而是說“自性真空”。這也是《維摩詰經》說的“空亦空”的道理。“佛性”之清凈中,沒有修行而成的“佛果”,也沒有業障纏繞的“眾生報”。“煩惱”就是“菩提”,“世間”就是“出世間”。有人達到這樣的“不二法門”境界,就可以稱他是變“眾生”而為“佛”,也可以說,他是即“佛”的“眾生”。
在《壇經·三六》里,慧能說:菩提本清凈,起心即是妄;凈性在妄中,但正除三障。……邪見是世間,正見出世間;邪正悉打卻,菩提性宛然。
慧能認為,自己心中有“邪見”,這就是“世間”;自己心中有“正見”,這就是“出世間”。但是慧能進一步提倡“邪、正”不二的道理,即已經超越“邪見是世間俗法、正見是出世間佛法”的差別觀念,這就是菩提性本來清凈的境界。他認為,頓悟自己本性不是用出世間法來破除煩惱分別的邪見。因為本來清凈的菩提不是離開妄想而存在的。如果有人從出世間法來破除煩惱而要作凈心,這也就是顛倒妄想。從此可以看出慧能關於世間領域和出世間領域之不二,比維摩詰走得更遠。
《維摩詰經》不僅論證世間也符合出世間的道理,還提出出世間甚至不能脫離世間而存在,出世間如同蓮花一樣,只有長在世間的污泥中,才能開出更好的花。在煩惱中覺悟本性的這種思想,在《維摩詰經·佛道品》里,很明確地提到:
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痴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有佛種。……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繼承這些思想,慧能很明確地闡明在修行解脫上沒有“出家、在家”的區別。在《壇經·三六》中,慧能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凈,即是西方。
為“不失本宗”而宣揚“三十六對”不二法門時,慧能還進一步提倡“僧、俗”不二思想。慧能的這種法門對中國佛教有著相當深刻的影響,使中國佛教具有濃郁的居士化佛教特徵。
總的來說,《壇經》是先主張要證得常清凈的“佛性”,然後提出“無住為本”說來規明“佛性”不是絕對的,永恆不滅的實體,“佛性”就是對“念”之“體”的相對說法。最後,慧能宣揚人的心性本來清凈,在此“人性本凈”狀態下,沒有“眾生”與“佛”,“僧”與“俗”,“煩惱”與“菩提”等差別相,這就是無所分別而平等一如的“不二法門”境界。
三十六對不二思想
慧能為了“不失本宗”,提出“三科”和“三十六對”思想,這是禪師引導學人覺悟的一種指導法門。慧能是從不二思想角度來解釋“五蔭”、“十二人”、“十八界”“三科”思想的。在《壇經·四五》里,他說:自性含萬法,名為含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慧能闡述運用“三十六對”的方法,解釋說: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慧能防止人們執著於“有、無”、“是、非”等兩邊,因此指出得到“不二法門”解脫境界的道路。慧能將“三十六對”具體分為三:一、關於外境無情,有五個對法;二、關於語言法相方面有十二個對法;三、關於自性起用方面有十九個對法。筆者認為,修行人在修行過程中,逢到的困難、迷路和障礙之中,最容易逢到而最難突破的是執著於外境或執著於法相、或執著於我相等的障礙,有的時候自己也不知道這種執著的病痛。因此,慧能把執著現象分為這三個方面,而讓弟子們作為接人的“活句法門”,這是慧能對《維摩詰經》“不二法門”思想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後來成為禪宗修行和說法的指南。
一、如果有人執著於外境(即外物),用“外境無情”的對法來解縛,他在這里提到五個對,即是:“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
二、如果有人執著於哲理、道德等法相,用“語言法相”的對法來解縛,慧能在這里提到十二個對,即是:有為無為、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
三、如果有人執著於心理作用方面,用“自性起用”的對法來解縛,他在這里提到十九個對,即是:邪與正對,痴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慈與害對,喜與嗔對,舍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常與無常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體與用對,性與相對,有請無親對。
關於這三十六對,慧能說:解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相離相,入內於空離空。著空即惟長無明,著相即惟長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雲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這些說法的意思是,佛教一切經論,說到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列出眾生所執的妄相,並破除這些妄相。而所有的妄相最終又都可歸結為很多對二分對立的相,大致說來,即慧能所列的三十六對。而破除這些妄相,就又可歸結為破除這些二分的對立,即歸結為不二。因此,慧能講三十六對以及破除三十六對,就是講禪宗的根本法門是破除二,歸於不二。而不二又無所破,這就已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領域,只可實證了。這就大同於《維摩詰經》之不二法門。
從哲學思想的角度看,《金剛經》和《維摩詰經》都是宣揚“般若性空”的“中道不二之門”,但從實踐精神的角度看,這兩部經典有所不同。《金剛經》著重於精神方面的解脫,而《維摩詰經》著重於闡明一種從自己生命存在的當處開始,不離開現實生活的修行解脫法門。慧能繼承而發展的主要是《維摩詰經》的這種精神,後來道一禪宗一派主唱的“平常心是道”等概念(在日常生活當中解脫的精神)是與此一脈相承的。慧能《壇經》的心性本凈、內心求佛、頓悟成佛和不二法門精神,都主要來自《維摩詰經》。而且,這四種精神的核心——不二法門精神,以及居士佛教精神,都與《維摩詰經》相一致。怪不得,慧能在《壇經》中最多引用《維摩詰經》。慧能《壇經》和《維摩詰經》的重要關係長期不被人重視,他的居士佛教精神,他重視實際生活的精神,他重視人民大眾的精神,也因之不被人重視。
(原載《北大禪學》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