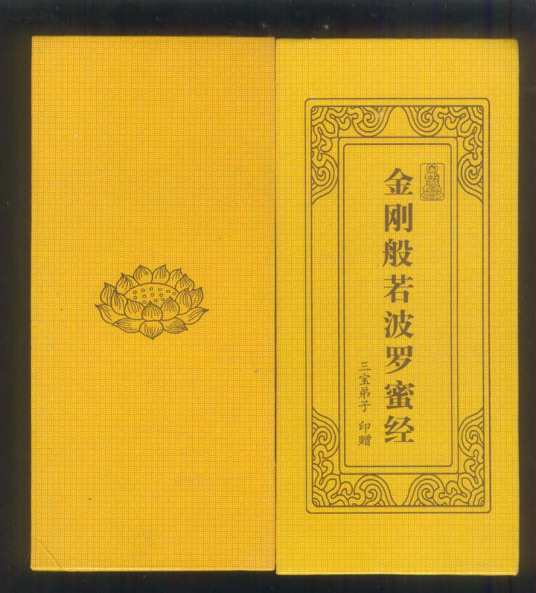《金剛經》是佛經中流行廣泛的一部經典,是大般若經的精華所在,也是禪宗弘揚的主要經典之一。佛經中說“般若以為母”。[1]般若是佛母,所有的佛和法都由其出生,但是對於佛、佛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都不能執著。所以《金剛經》中說“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在《金剛經》的義理中,存在著語言和實相的矛盾。佛陀教誡諸大菩薩悲智雙運,既闡發了廣大的菩提心,又開顯出破除種種執著的般若智慧,直指菩提,卻又無所得。
一、言說和非言說之間的矛盾佛陀教導諸菩薩突破語言的局限和障礙去了悟佛法的真實內涵。“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2](p749)語言本身存在著局限性,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總是二元對立的,即語言和表述的對象分離,當想要表達超越二元對立的實相時,語言無能為力。在使用語言通向實相的過程中語言只是暫時的工具,必須超越語言使用過程中二分的形式去體悟實相。實相是不可以言說的,《金剛經》中“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靜。即生實相。”“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語言直接指示思想和概念,並非實相。實相是離於言說的,但是靜默又不可以說明實相。語言的表達具有種種的局限不能確切指稱,例如人們談論火時並不能火燒舌頭,談論食物時也不能感覺到肚子飽。所以在談論任何一個存在時,它指稱的只能是名詞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在佛教中稱作比量,而非現量,《金剛經》中用語言來表述實相,同時為了在使用語言時突破語言的所指,慈悲的佛陀隨時對語言概念使用過程中所生起的執著進行破除。因此經文採取了獨特的言說方式:用語言來說明實相,但是為了避免眾生因此產生對於語言的執著,因此說過即掃,邊說邊掃,形成了《金剛經》獨特的語言句式“(佛)說……即非……是名……”既要言說,同時也避免言說所產生的執著和障礙。例如: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2](p751)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4](p750)《中論》中言“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語言在言說過程中的局限性不僅體現在無法表述超越二元對立的實相,而且語言運用的概念名相都是我們的感覺器官所能認知覺察的現象,是一種假名施設,而對於我們的感知器官(六根)所不能捕捉的現象界背後的東西,語言就失去了言說的能力。
佛陀藉助語言工具來說明義理,但是要闡述的義理又不是語言可以完全清晰表達出來的,因此在語言使用的過程中一邊使用語言,一邊破除語言的局限和障礙。這就採取否定性的言說方式。《金剛經》語言的這種特點,已經有學者作過研究:般若的特點在於去執、在於否定。第二句“即非”否定了第一句所舉之“法”的真實性,但般若並不是單一的否定,“即非”一句缺乏辯證通融之處。只有否定第一句的非實性,又否定第二句的極端性,達到更高一層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是金剛般若的理論特色所在。“是名”一句的價值就在於此,它是雙重否定的終結,既包含“非實”性,也包含“非虛”性,“非法、非非法”,空、有對立而又統一,即後來所說的“真空”不礙“妙有”。“非實”故不應“取”、“住”,而應離一切塵染,“生清凈心”;“非虛”,故不應“斷滅”,而應方便起行,“修一切善法”。這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的基本特色。[3]
佛陀用語言開示出的種種佛法內涵只是指示人們到達真理彼岸的工具,而並非是真理本身。就如同人們的目的是到達河岸的對面,因此需要乘坐渡船,但是當到達對岸之後渡船就應該舍棄了,不能扛著渡船繼續前進。“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
在《金剛經》的末尾通過佛陀和須菩提的問答又一次強調了語言的局限性,使用語言所指的概念要和實際存在區別開來,要了悟佛法的智慧一定得克服語言的局限性,突破語言的障礙。“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對於修行佛法的人,對佛法中任何一個名相,任何一個法,包括佛陀、菩薩及種種經典都應該有這種不執著的灑脫精神,才能真正領悟佛法的內涵。
二、《金剛經》經文中的菩薩悲智雙運的修行次第《金剛經》是佛教的般若類經典的精華,反復闡述了菩薩發菩提心後,應該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其心,如何讓心以無所住而安住的大智慧。
《金剛經》的經文中雖然是須菩提請問的,但是《金剛經》並不是為普通的二乘人所說,而是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二乘和大乘人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是否有菩提心,這就說明了《金剛經》的言說對象是發了廣大菩提心的菩薩們。所以在經文開始須菩提請問時,“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而世尊在回答時,特別強調兩點:一、發廣大心,側重在菩薩修行的悲心上,度化的不僅僅是一部分眾生,而是“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而滅度之”。發心之後要度盡如此種類眾多的眾生,而這些眾生,並非真正外在意義上的眾生,如同六祖曰:“卵生者,迷性也,胎生者,習性也。濕生者,隨邪性也。化生者見趣性也。迷故造諸業,習故常流轉,隨邪心不定,見趣墮阿鼻。起心修心,妄見是非。內不契無相之理,名為有色。內心守直,不行恭敬供養,但言直心是佛,不修福慧,名為無色。不了中道眼耳見聞,心想思維,愛著法相,口說佛行,心不依行,名為有想。迷人作禪,一向除妄,不學慈悲喜舍,智慧方便猶如木石,無有作用,名為無想。不著二法相,故名若非有想。求理心在,顧名非無想。”[4]這裡,六祖對種種眾生的心理狀態進行解釋,暗含人們心中的種種執著習性即是不同類型的眾生,心性不同產生種種差別,如同《金剛經》中雲“眾生眾生者,即非眾生,是名眾生。”
發心之後的第二步側重在菩薩修行的大智慧上,發了廣大菩提心之後要運用空觀去超越對於內在的自我、外界的眾生、佛法等的執著,最後達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清靜。在《金剛經》經文的敘述中,釋迦牟尼佛逐層破除菩薩,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的種種執著。首先總體說明發了菩提心的大菩薩們要發願度盡一切眾生,但內心卻十分清靜,明了實無有眾生可度者。然後逐層破除菩薩在修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種種執著,先是破除人們對於佛色身莊嚴的執著,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引申為“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破掉對外在世界萬物現象界的執著,接著進一步深入,涉及到對佛法本身的否定,“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接著破掉對佛法自身所證之果“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而直接否定人們意識中所存在的佛法觀念。“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以及對於小乘各個階位成就的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相的執著,進一步強調佛於燃燈佛所,佛果也是實無所得,而菩薩對於成就的佛土也並非有莊嚴之心。“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接著佛陀又深化了對於所有外在事物現象、微塵世界實有的破除,以及進一步破除前面用來破除外在事物現象實存的工具——佛法的執著,步步深入,甚而破除了對於說出佛法道理的佛陀的執著,徹底清靜,而又沒有清靜之相。
須菩提理解佛陀的深意,甚深感動,涕淚悲泣進一步深化主題“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破除人們對於修行過程中六度萬行實有的執著。“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到此處菩薩用心的核心是“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這裡涉及到佛法中菩薩修行成就的兩方面,佛號為兩足尊,福德和智慧兩方面圓滿成就,這裡《金剛經》點出了佛法中菩薩修行的兩大核心:其一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具足大悲心,去上求自己的覺悟,下利無邊眾生,修持一切善法,積累福德資糧;而接下來是應無所住,離一切諸相,遠離種種執著,包括對佛法的執著。“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見種種色”。這就是勝義菩提心,並不僅僅是修持善法就可以了,而是必須要在修善法,積功累德的同時,能證入無我的空性,了達所有的善法都是如夢幻泡影,不應該有絲毫的執著,成就智慧資糧,這樣菩薩才可以最終修行成為福智具足的兩足尊。
總之,《金剛經》中暗含菩薩的三級修行次第:首先要發願菩提心才能預入菩薩之列:“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次,發心之後要有廣大的行動,修行一切善法,實踐六度萬行去度化所有眾生,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等,即是行菩提心。“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再次,證悟勝義菩提心。修行善法的過程中,破除所有的佛法的執著,了悟空性智慧。“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對於紅塵中普通人來說,都具有貪嗔痴慢疑,對於外界執著的心非常強烈,在世俗的生活中,貪愛名利財色,求之不得嗔心大發,有些人雖然平日心情平靜,但遇到境界時也不能自拔,生活在自己念念相續的無明中,痛苦時滿眼愁緒,山河悲咽,而愉快時草木歡歌,心態使外境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強烈的自我執著帶來很多痛苦。要離開痛苦徹底解脫,覺悟成佛才可以達到。所以要發菩提心,立下誓願“為利有情願成佛”進入菩薩修行的系列;但是一般人接觸佛法以後,又會把過去黏著的習性擴展到學習佛法的種種執著,佛陀說善法,就執著於善法,而說阿羅漢,就執著於阿羅漢,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不能放下,粘著在佛法的名詞概念上愈發執著,而《金剛經》就是側重來破除菩薩們在第二個層次上的執著之心,雖然佛陀教導眾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但是當做到眾善奉行時也還不是究竟的境地。第三個層次上勝義菩提心就是了悟空性智慧的,即自凈其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要破除對於善法的執著之心,雖然眾善奉行,但更重要的是自凈其意,以無所住的心,無取相的心來躬行一切善法。破除人們對於佛、對於佛所說的善法的執著,“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並且毫無希望回報之心,這才是真正的菩薩。
三、《金剛經》的超越式理性和現代人的生活上文對《金剛經》的語言表達形式和敘述內容作了簡要說明,那麼這部經的現代意義是什麼呢?《金剛經》是治療現代人心理煩惱的智慧妙方,是破除各種執著的利劍,它教人用大智慧來面對一切境界,無論是外在的現象界還是內在的種種心理,破除常人心中佛、佛法、菩薩、阿羅漢、菩提等概念的執著,真正無所住而生其心,擁有清靜喜悅的生活和放下執著的灑脫。
首先,《金剛經》指導人們過一種理性指導下的慈悲和智慧具足的生活。現代人崇尚理性,而《金剛經》中講的正是脫離迷信外在崇拜等宗教因素的大智慧。《金剛經》中不停地破除人們對於佛、佛所說的法、佛所證的果、外在的微塵、世界、凡夫、眾生、菩薩等的執取,雖然破除這一切,但並不是說沒有,而只是一種假名施設。在這個過程中,提供給現代崇尚科學理性的人們很好的修心之法。經中對於如來、佛就有非常理性的描述和認識:“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在這裡不僅破除人們對於寺廟中金光閃閃的大佛的執著,佛並不是外在的能夠給人一切願望滿足的崇拜對象,而且也消解了對佛法神秘化的認識,而把它落實到實際生活的種種現象上,“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法”指一切的事物,不論大的小的,有形的或是無形的,都叫做“法”,不過有形的叫做色法,無形的叫做心法。經中明言一切法皆是佛法,可見佛法並非神秘不可測,遠離人們現實生活的高深哲理,而是能給與人現實生活指導的大智慧。
現代人的種種痛苦焦躁來源於自我執著的深重,種種攀緣心所帶來的焦慮,無非是內心執取某個事物,由於不能獲得而產生內心的痛苦和情緒的反應。巨大的工作壓力,緊張的生活節奏都讓人們煩躁易怒甚至抑鬱。《金剛經》提供給現代人智慧慈悲指導下的理性,從自己內心出發,善護其心,明了“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放下種種的執著妄想,去體驗心靈深處的清靜本性,給生活節奏緊張,心情焦慮的現代人提供心靈的清涼劑,亦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講“依般若波羅蜜,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這裡的涅並非指灰身滅智的死亡,而是指徹底熄滅煩惱,獲得清涼自在。《金剛經》中教給人們以無所住心、清靜心,面對生活中一切境界,自然就可得到清涼喜悅。
其次,《金剛經》提供給人們無所執著的道德律令,成為灑脫的自在人,同時又行善去惡。《金剛經》甚至於可以說是自然的道德律令,即“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這裡強調以無所得的心修持善,突破有的人做慈善事業圖名圖利之心,而成為自覺自願的自然行為。《金剛經》不僅破掉人們日常生活中對於自我執著帶來的種種造惡的執著、而且破掉佛法修為中的對於善法的種種執著、沾染,最後達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指導菩薩以“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也是我們現代人應該具有的身心修養境界,不執著於自我的惡,也不執著於利他的善,在如夢如幻中修行一切善法,連善也不執著,如是清靜,喜悅才能獲得灑脫自在。
參考文獻:
[1]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卷3)【z】。大正藏(30冊)。台灣:中華佛研所,2008cbeta,828c.
[2]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z】,大正藏(8冊)。台灣:中華佛研所,2008cbe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