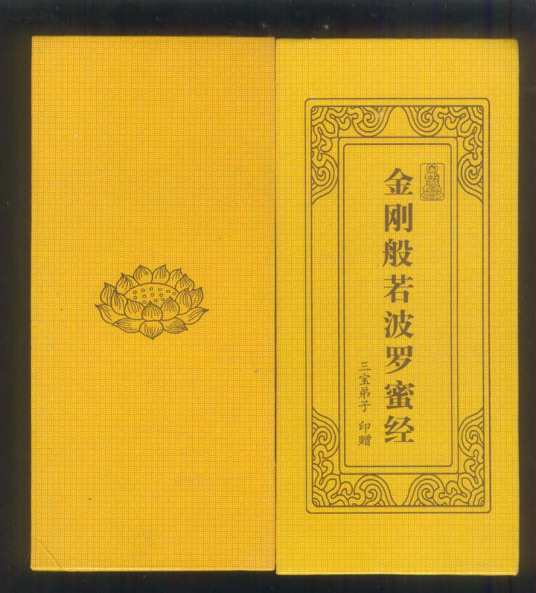曲槐
綜觀《金剛經》,不但有其清晰的主題,並且其邏輯結構也很嚴謹,層次分明,一目瞭然。這無不說明佛陀說法度生的權巧方便、化導有方;譯人的翻譯水準之高超,義理組織之周詳,於此可見其一斑矣。
據說古印度的邏輯學就是人們常常所說的“五明”中的因明學,所謂的“宗、因、喻”三。 “宗”就是指所立的論題; “因”就是為了說明“宗”之所成立的緣由; “喻”就是用淺顯易懂的比喻、事例說明“因”所闡述的道理。即就是先“標宗”,立論題,次“述因”,擺事實、講道理,後“舉喻”,舉例子、打比喻,以做進一步的淺近說明,以達到預期的功效。也是“宗——因——喻”這樣一個循環的過程。佛陀當年說法也採用這種因明邏輯,也就是說以“宗、因、喻”的形式進行闡述、論證佛法的真理。
作為邏輯學的一種,因明又與內明有所不同,內明是指佛教的內典因明學。而因明的宗又與佛典的宗有著根本不同的內涵,因為佛典的宗是整個佛法的核心部分,也是佛陀說法的宗旨所在。如小乘佛典的宗旨是以明“人空”為主,大乘佛法的宗旨是以明“法空”為主。一般的經只有一個宗,如《佛說阿彌陀經》以信願行為宗, 《金剛經》以發菩提心為宗等。因明的宗是論辯者自身所要闡明的觀點,像這樣的宗,一部佛經可以有很多個。在因明學中,宗、因、喻三是同等的重要,若無因,宗則難以成立;若無宗,因則無所歸;若無喻,則難以說明因之正確,宗之成立。所以,標宗、述因、舉喻三者是同等的重要,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
佛陀在《金剛經》中,為了開啟人們的菩提心,發揚菩薩的入世度人精神。圍繞須菩提的三問,首先闡述欲發無上菩提心者須先“降伏其心”的必然性,次則說明菩薩廣行六度時應“無住生心”的不可或缺性,後則詳述諸佛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深奧道理。這是告示人們,由因趣果的一條層進式的漸次修行道路,也是佛陀說法遵循因明邏輯規則的明證,使抽象難懂的道理顯得有條理化,也易於人們理解接受。
在《金剛經》里,佛陀為了論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重要性,大概分了三步進行論述。因為此句是全部經文的節骨眼,是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遠離“四相”的具體落實,是菩薩“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必由之路。佛陀有次第地先開示人們,要遠離四相樹立佛法正確知見。如經雲: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 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接著又示其“住心”之方,令其付諸於實踐。如經雲“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最後佛陀又結示受持、讀誦、演說、流布此經的種種福德,勝於“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祗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的福德。而流布此經的最佳方式在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陀這種由“觀念——行為——觀念——行為”,互為里表,層層深入的,像“庖丁“解牛”似的論證方式,是有很強的邏輯征服力的。為了證明自己所說的正確性,啟發人們的深信心,破除人們的疑惑,不惜唇舌地花費了大量時間宣說了種種菩薩所應行的理論根據。就如在正宗分中,佛陀接二連三地問了三十個“於意雲何”,分別就十方世界、如來色相、五眼六通、小乘四果、授記有無、布施忍辱、來去有無、諸相非相、菩提無法、凈土度生、說法有無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激烈精彩的論述。終於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角度出發,徹底打破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僵局;以“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無相行施精神,唱出了“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的寒梅考驗,證明了“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的千古鐵案。
作為因明的邏輯學,不是完全專註於空談理論,而在於舉例及喻說,以期達到人人心悅誠服的真實可信才行。為了說理的透徹,特別是為了能取信於人們, 《金剛經》中就列舉了許多的事例,並以恰如其分的比喻作了說明。如在闡述“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以佛陀自己的往昔修因事例作了有力明證,文雲: “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在闡述得諸佛授記無法可得的道理時,又以自己當年得記為例說明,經雲“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說明。
為了發揚“無住行施”的菩薩道精神,可謂是佛陀苦口婆心,以“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的身份,告慰須菩提說: “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又恐眾生難以徹底深信奉行,則以種種譬喻說明了住與不住的利害關系,如文雲:“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經中像這樣的比喻是很多的,舉不勝舉,不再列舉說明。
綜觀《金剛經》經文:主要是以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貌三菩提心為宗,展開了探討,以種種譬喻、因緣、本生等故事為證據,說明“離相伏心”、 “無住生心”的般若妙用,此經除了“發菩提心”這個大宗外,還有幾個小宗,也都採用了同樣的說理方法。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等。當然這些小宗也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關聯的,都是圍繞“發菩提心”這個宗趣而服務的,相互間的歸趣是統一的。
總之, 《金剛經》體現出了因明邏輯學的宗、因、喻的特色,再加上優美的語言文字,具有很高文學價值的。從宗而因,由因而宗,因宗一致的邏輯推理來說,可謂是達到了恰到好處的境界。而其中的“喻”說體現出了佛陀說法普被三根的悲心,也為經文增添了色彩,處處顯示了經文組織結構的嚴謹,讀後回味無窮。
摘自《寒山寺》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