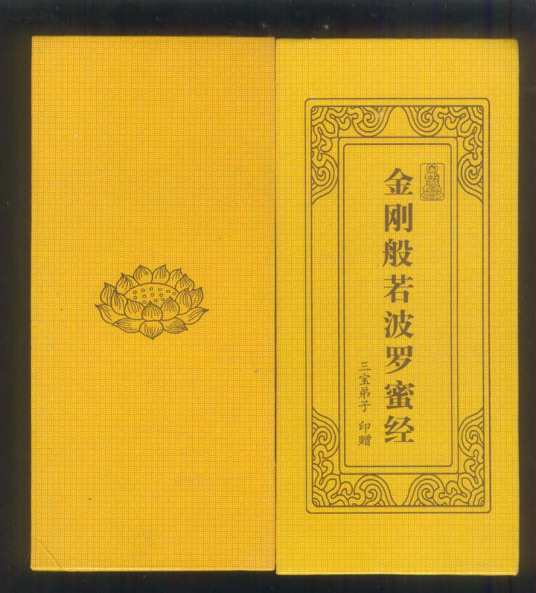何為“冥世偈”?
資料一:
鳩摩羅什所譯的《金剛經》,大致在唐五代前後,不同流傳本有一很大的差別——按昭明太子之三十二分法的《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中,晚出本多了六十二個字: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資料二:
昔長安溫國寺僧靈幽忽死,經七日見平等王,王問和尚曰:“在生有何經業?”靈幽答曰:“持金剛經。”王遂合掌請念。須臾念竟王又問曰:“和尚雖誦得此經,少一偈者何?”靈幽答王曰:“小師只依本念不知缺何偈?”王曰:“和尚壽命已盡,更放十年活。此經在濠州城西石碑上,自有真本令天下傳。”其僧活,具說事由矣。〔1〕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敕令寫此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資料三:
署名六祖慧能的《金剛經解義》中,對上述六十二個字有這樣一段“解”:
靈幽法師加此。爾時慧命須菩提以下六十二字,是長慶二年,今現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記六祖解在前,故無解,今亦存之。〔2〕
二、問題的提出達照法師的《〈金剛經贊〉研究》收集了二十多種敦煌遺書,將從《金剛經贊》到《傅大士頌》的演化分三階段。〔3〕在推斷其第三階段(《金剛經贊》)演變為《傅大士頌》的年代)時,達照法師指出:“它們〔4〕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加了羅什譯的《金剛經》,且該《金剛經》有靈幽法師所加‘冥世偈’。因此,加入該經文的傳本,最早也是在公元822年之後才出現的。”〔5〕按:公元822年即是長慶二年。雖然著者很謹慎地推論,不能排除一種可能:即在“冥世偈”出現之前,《金剛經贊》已經演變為《傅大士頌》,等到“冥世偈”出現之後,有人將其加入《傅大士頌》中,從而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流傳形態……如果上述假設能夠成立,則《金剛經贊》是否在公元822年至公元831年之間演化為《傅大士頌》,也需要再研究。〔6〕
但就本文所關心的主題而言,達照法師對“冥世偈”中“長慶二年”的說法,是深信不疑的。同書中還提及,他的結論同四川大學張勇博士的看法“大體相當”。查張勇博士之《傅大士研究》,在依據“冥世偈”來推斷這一點上,二人是完全相同的。敦煌寫本闡述的經文既同於今傳羅什譯本,四十九頌、五歌要當創撰於長慶二年以後……總之,《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應創撰於唐穆宗長慶二年(822)至文宗太和五年(831)之間。〔7〕
舉此二例,筆者想問的是:這樣的依據“冥世偈”故事、特別是相關的“長慶二年”來作考據,是否有商榷的餘地?其實,台灣國立聯合大學何照清教授在她的《慧能與〈金剛經解義〉》一文中,就已經提出這個問題了。
當何教授在考察《解義》的成書年代時,該書中“冥世偈”部分的“解”理所當然地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是疑問多於肯定:“此段話若屬實,則是探究《金剛經解義》形成時間的重要關鍵。長慶二年是西元八二二年,若此話屬實,可證明《解義》在西元八二二年以前已經出現……那麼這段話是否真確?”何教授還給這段話加了個腳註,頗能道出她連續兩個“若此話屬實”的心情:
今見早於慧能的窺基(632—682),所作《金剛經贊述》已有“爾時慧命……”以下六十二字,且有窺基的述語:“舍衛漏此文,世親此第三疑……”。若窺基時已見此文,則“靈幽法師加此”之說就不正確。但《續藏經》所錄,在窺基此六十二字上亦有“恐後人所補”的附語。那麼此六十二字到底何時所加?或許也是探討《解義》形成的重要關鍵。然今見唐朝書家柳公權於長慶四年(824)所寫《金剛經刻石》也未有此六十二字;因此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8〕
三、考“長慶二年”本來,這“冥世偈”故事真也好,假也好;羅什譯《金剛經》中有這段話也好,沒這段話也好,對我們理解《金剛經》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或者說,它只有宗教意義而無學術意義。但正因其中有加進了“長慶二年”四字,那它的意義就非同小可了。
回顧前面已列出的資料,法藏敦煌p2094號《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和宋高僧傳卷二十五的《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二者都沒有“長慶二年”四字。而首次出現“長慶二年”說法的,當是署名六祖慧能的《金剛經解義》。
據《敦煌古籍敘錄》考,《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的十八則靈驗記中,有九則與初唐人撰述相同,故該記當作於初唐或中唐之時,〔9〕當為現在能夠見到的“冥世偈”故事的最早資料。馬上有人會問:慧能大師的《金剛經解義》,不也是中唐以前的作品?對此問題,回答如下:
當然,如果《解義》真是慧能的作品,那麼《解義》就應當成書於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出家)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入滅)間。
雖然有文獻資料提及,有慧能說《金剛經》的記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2170《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中(圓珍於唐宣宗大中八年,西元854年),有《能大師金剛般若經訣》一卷;2172《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中(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857年),有《金剛般若經訣》一卷;2173《智證大師請來目錄》中(智證“即圓珍”於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西元858年),有《金剛般若經記訣》一卷(曹溪)。另,《新唐書·藝文志》卷五九,載《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六《經籍考》五十三中,錄《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但上述資料,支持度不夠!一卷本的《訣》、《口訣正義》、《解》,與二卷本的《解義》,終究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而反過來,否定的證據,卻有力得多。
首先,沙門智?撰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的《開元釋教錄》,未見六祖《解義》。此時距大師圓寂不到二十年,而《開元釋教錄》的體例完備、考訂嚴密,是人所共知的。
其次,何照清教授的四點質疑,似乎無法迴避:一、慧能及其弟子,尤其是神會的相關文獻中,都未提及慧能注《金剛經》事;二、明末憨山大師,以“中興曹溪”為行願,其《金剛決疑》,卻沒提到六祖注;三、歷代中國人編的《大藏經》,都沒有收入任何一種慧能注《金剛經》;四、迄今為止,引用《口訣》或《解義》者,全是宋以後的作品。〔10〕
所以,雖然古往今來學者們作了諸多研究,有的說現行二卷本《解義》非慧能所說,有的說思想上還是慧能或其後裔的,〔11〕但無論如何,就筆者論證目的而言,二卷本《解義》晚出,當是肯定的了。
既然如此,晚出的《解義》,卻比早出的《靈驗記》多了精確的年代,怎不叫人起疑?
如果我們因無法確定《解義》到底晚到哪一時代,而將目光轉向下一件記錄“長慶二年”的資料的話,就要一下子跳過數百年,才能看到刻於南宋淳熙六年(1179),道川依《解義》注的《金剛經注》,再次重提“長慶二年”故事。〔12〕道川的活動年代,在南宋建炎年間。他的《金剛經注》後來被收入南宋紹定四年(1232)楊圭所編四卷本十七家釋義,後洪蓮演為五十三家注四卷。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間閱諸編,選其至精至要、經旨弗違者,重加纂輯”,摒除五十三家本中傳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分分目,略減注者數家,裒成一卷《金剛經百家集注大成》,道川注幾乎全數收入。由此可見,以“長慶二年”為標志的“冥世偈”故事,要到宋明以後,才得廣泛流傳。
四、考“冥世偈”故事宋明以還,雖然挾六祖之盛名,“冥世偈”故事頻頻出現於《金剛經》的註疏之中,但寫《宋高僧傳》的契嵩和尚,照錄了《靈驗記》的故事後,卻公然斥其“妄釀”,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疑豫,必招詐偽,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誡之哉!”〔13〕
在科學主義盛行的今天,“冥告”之說,當然不值一駁;但筆者對故事中“冥世偈”是從濠州鍾離寺石碑上抄得之說,也持否定態度。本來,羅什本缺一段,補以魏譯,是不言而喻的事實。
筆者曾將現存的《金剛經》六種譯本的電子文本,去掉所有的標點,在電腦上用校對軟體,把羅什本同其他五本一一對校。在軟體要求一處差異不超過六十字、或差異處不超過五百個時,惟有秦譯和魏譯的對校能完成,其他四本的差異處都要超過八百九十個。檢查秦譯和魏譯的校對結果,全部一百一十段文字,“冥世偈”不算的話,完全沒有差異的僅七段:
須菩提於意雲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對照的結果說明:羅什本同其他五本之間,完全相同的段落極少;但相對而言,羅什本同魏譯的風格最接近。因此,說羅什本的這段缺文,從魏譯中移得,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結論。當然,現在的問題是,這移植是怎樣完成的,是如契嵩和尚所相信的那樣“靈幽獲鍾離寺石經”還是要早得多?逝者如斯,我們不可能找出確切的時間地點,但歷史的蛛絲馬跡,還是有可能追溯的。
按:《新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濠州鍾離郡上:“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土貢?綿、絲布、雲母。戶二萬一千八百六十四、口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縣三:鍾離、定遠、宿州。
據此,我們只要在元和三年(808)前,凡對羅什本《金剛經》註疏者,在其中找到關於秦本缺失,補以魏譯的證據,則關於“冥世偈”抄於鍾離寺石碑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了。近人江味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所附《金剛經校勘記》雲:“按此六十二字,秦譯本無之,乃後人據魏譯增入者。故肇注乃至纂要,皆未釋及。惟贊述已引魏譯加入釋之。大約唐時或加或不加,至五代以後本,則無不加入耳。”
江氏一生,與《金剛經》尤所努力,其《金剛經校勘記》亦相當精要。他指唐窺基(632—682)《金剛般若經贊述》(《大正藏》1700)中已經引入魏譯,照理說,當為定論,但卻還是有人持疑。據該本文首日僧順藝(志道)所寫的“校訂例言”:“本經新翻未容潤飾,故此疏就什譯以解之,蓋以其譯在初,流傳最廣耳。然有什本所闕一二,以余本補之者,今圈其右方而注之於格上。”故他在“冥世偈”的位置上批道:《會釋》亦雲“什本闕無此一段文”,然藏本皆有文,恐後人所加補。 〔14〕所以,光憑一本《贊述》,孤證不足,因此,我們需要再提供更多的證據。
證據之一:
隋吉藏(549—623)《金剛般若疏》(《大正藏》第1699頁)。按:吉藏此疏,以“玄意十重”統領全文:“一序說經意,二明部儻多少,三辨開合,四明前後,五辨經宗,六辨經題,七明傳譯,八明應驗,九章段,十正辨文。”其第十“正辨文”部分,原文不分章段,經文和疏混在一起。筆者將疏中的經文一一輯出,發現全部是逐字逐句對羅什本作疏的,唯有在“冥世偈”的位置上,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現象:
問:何等人能信此法耶?答:論偈雲:“非眾生眾生,非聖非不聖。”此人非凡夫眾生,故言非眾生。而是聖體眾生,故言眾生也。非眾生故非聖,是聖體眾生,故非不聖也。
問:若言凡夫不信,不可為凡;聖人能信,不需為聖。今說此經,竟為何人耶?答:觀此論意,具足顛倒有所得,凡夫不能了,此是習無所得觀,眾生則能信。此眾生望有所得人,故非眾生,未具足了悟,故非不眾生也。(按:標點系筆者另加)
很清楚,吉藏當時用的羅什本里沒有“冥世偈”;但他肯定注意到,這兒有缺文,因為他在這個位置上,引用了相對應的“彌勒偈頌”。
相傳無著菩薩,升兜率天兜率宮慈氏尊處,就《金剛經》義請益彌勒菩薩,得彌勒菩薩七十七偈。無著轉教其弟世親(又名天親),世親菩薩依照其教造論作釋,並加進歸敬偈二(首),結偈一(尾),於是就有了傳世的彌勒菩薩八十偈。自古以來,這彌勒菩薩八十偈就是理解、修習《金剛經》的權威性依據,無數高僧大德關於《金剛經》的註解疏論,都依經引偈,然後引申發揮。
檢索經藏,彌勒偈頌有元魏菩提流支(《大正藏》151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和唐義凈(《大正藏》第1514頁《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二種譯文。吉藏所引,乃是流支譯本。而問題的關鍵是,在流支譯本中,這“非眾生眾生,非聖非不聖”所對應的經文,恰恰就是後世出現在羅什本中的“冥世偈”!無論說吉藏是有意的選擇,還是無意的引用,他已經開啟了以魏譯補秦譯的大門。
證據之二:
就是日僧順藝據以存疑的,窺基的另一著作《金剛般若論會釋》(《大正藏》第1816頁),此乃迄今為止最早的一本,把《金剛經》不同譯本逐字逐句相互對校的大手筆。《會釋》以“二論”〔15〕為綱領,對校玄奘、羅什、流支、真諦四種譯本,條理經文,抉發經意。大師的優勢,在於他當時身居大唐帝國的皇家圖書館,收藏之富,無與倫比。諸譯的底本,隨手可取:
顯慶年,於玉華寺,所翻大般若。勘四梵本……經本自有廣略中異。杜?廣本,能斷文是略;於闐本羅什文同;中者是天竺本,與真諦流支本同。玉華更譯,文亦相似,今於慈恩梵經台,具有諸本。〔16〕
故《會釋》所提供的信息,當有權威性。在釋“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這段經文時”,《會釋》解道:
又,《論》次解“信佛法人”雲:“是人則為第一稀有者,顯示說第一義,是不共及相應。”此解意雲:今欲信佛語人能利益。信佛說“彼非眾生”,此約第一義,顯不共義;信說“非不眾生”,此約俗諦,顯相應義。此人難及,故言“第一稀有”。請本皆無此文。……世親《論》雲:“所說說者深,非無能信者。非眾生眾生。非聖非不聖。”上兩句正答前疑,釋善現問。下之兩句解如來答,此顯能信是經者,非是凡夫眾生,故言非眾生,乃至聖眾生,故言非不眾生也。什本闕無此一段文。(按:標點系筆者另加)
這一部分,窺基大師校出了二處差異,一是《論》中有“是人即為稀有第一”文,而四種“請本”都缺譯。二是明確點出,羅什本缺了這整段經文。
這兒需要強調的是,前文的“以《二論》為綱領”一句,絕非泛泛而談。窺基這本《會釋》,從頭到尾是按照無著菩薩傳自天竺的“七義”“十八住處”而展開的。歷史上《金剛經》的科判有五種之多,“七義”、“十八住處”傳入最早,而且是“無著稟偈於彌勒,天親受旨乎賢兄”,其權威性不容置疑。請看上文中的《論》之原文:
論曰:此下“上求佛地”中,“心具足”。於“心具足”中復有六種:為念處、為正覺、為施設大利法、為攝取法身、為不住生死涅?、為行住凈,應知。於“心具足”中,為“念處”故。經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如是等,此處“於諸眾生”中,顯示如世尊念處故,“彼非眾生”者,第一義故;“非不眾生”者,世諦故。“是人即為稀有第一”者,顯示說第一義,是不共及相應故。此文如前說。〔17〕 (按:標點系筆者另加)
清清楚楚,窺基所校出的羅什本缺文,屬“第十八住”所說“六種具足”的“心具足”之第一“念處”。
所以,窺基說“什本闕無此一段文”時,不是就此一句,交代一下就完事了,而是在四本對校的基礎上,指出他本均有而什本獨缺;是在對《金剛經》結構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什本所缺,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體系環節上的缺失。
對照綿密的科判,環環相扣的體系缺了一段,當然需要補上;而更有現成的譯本可資,則秦本缺失,補以他譯應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但據前引首日僧順藝為《贊述》所寫的“校訂例言”中,有“本經新翻未容潤飾,故此疏就什譯以解之”一語,好像是《贊述》在前(玄奘譯本剛出)而《會釋》在後(已經四本對校了)。如果順藝之說成立,那先成的《贊述》以魏譯補入,而後出的《會釋》則付之闕如,就好像說不大通了。所以,雖然《會釋》揭櫫了補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贊述》則已經付之實行,在不知窺基的《贊述》和《會釋》孰先孰後之前,還是無法解決出於同一人之手的二本著作中,這六十二個字一有一無的矛盾。
證據三:
曇曠生卒年不詳,但據敦煌遺書英藏s2732,曇曠所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標明“其時巨唐大歷十九年歲次‘寅三月二十三日’”。〔18〕時為公元774年,當為曇曠的活動年代。
曇曠的《旨贊》,其體例為“經。xxx至xxx贊曰……”。全書二百六十六處“經……贊曰”,全部用羅什譯本,惟有所謂“冥世偈”的地方,既無“經”,也無“贊曰”。
次下第六明心具足,於中准論有六種心:一念處、二正覺心、三施設大利法、四攝取法身、五不住生死大心、六行住凈心。於中第一念處心,經顯第十八,何人能信疑,而斯經亦闕此經文,余本即有。故《論》列之,如魏本雲:“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此中意者,菩薩如佛常念眾生,若善不善、若信不信……無著約等念而令悲名念處心;天親約有信而令名顯何人能信疑。故《論》頌雲:“所說說者深,非無能信者,非眾生眾生,非聖非不聖。”雖然還沒有像後世那樣,直接列“冥世偈”為秦本的組成部分,但曇曠將魏譯嵌入秦譯之舉,已經非常明確和完整。此時雖距窺基在世已有百年,但離元和三年(808)及長慶二年(822),尚有幾十年之遙。
當然,歷史的變遷,一定是一個過程,會有過渡,所以江味農《金剛經校勘記》說:“大約唐時或加或不加”。像柳公權書《金剛經》於長慶四年(824),依然堅持羅什本原貌,即是例子。〔19〕但有上述數例作證,從窺基到曇曠,秦本缺文已是共識,補以魏本已開先例。大唐盛世,如此多的高僧大德、四眾弟子,恐怕不會再傻等半個世紀,方到濠州鍾離寺,抄得早就在魏譯中的“冥世偈”。
羅什譯本為什麼會漏了整整一段呢?諸說紛紜,不一而足。清徐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郢說》說:彌勒偈中已有之,古本焉得無之,豈古本原有而唐時偶失之耶?清俞樾《金剛經注》說:
古本所無,亦後人增益,蓋以佛言無法可說,恐人因此不信佛法,故增益此文。其意謂眾生則不信,非眾生則自能信,所以堅人之信,與侈陳福德,其意正同,皆佛弟子護法之苦心也。
江味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所附《金剛經校勘記》說:秦譯蓋因前文已有如來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故此處從略歟。
近人道源《金剛經講錄》說:古時由印度帶梵文的貝葉本到中國來是很困難的,那時交通很不便利,由陸地到中國,要經過八百里的大戈壁沙漠,由海路來,隨時都有可能遇到風浪而喪失性命。梵文本子不是紙印的,是用貝多羅樹葉寫成的,如果搬運的中途,遺失了一片貝葉,或損壞了一片貝葉,那麼這部經就會少了一段經文。這部經如果少了一葉,絕對沒有人敢隨便添加進去的。何以故?因為譯場上,有千人以上,你隨便加進去,沒有強而有力的根據,人家是不會同意的,這是怕誤了眾生的慧眼。
印順導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說法則更深刻:本經,什公第一次譯出。除這,還有五種譯本……在六譯中通常流通的,即是什公的初譯。其後的五譯,實是同一法相學系的誦本;如菩提留支譯達摩笈多譯等,都是依無著、世親的釋本而譯出。唯有什公所譯,是中觀家的誦本,所以彼此間,每有不同之處。要知道印度原本,即有多少出入;如玄奘譯本也有與無著、世親所依本不同處。但想到前面提到過的,窺基大師著《會釋》時說得清清楚楚:
顯慶年,於玉華寺,所翻大般若,勘四梵本……經本自有廣略中異。杜?廣本,能斷文是略,於闐本羅什文同。中者是天竺本,與真諦流支本同,玉華更譯,文亦相似。今於慈恩梵經台,具有諸本,故上述種種,總覺得說服力都還不夠。
筆者的猜想,就是當年羅什所用的“於闐本”,本來就缺了這一段,結果造成了後人無數困擾,還引出了這樣一段公案。總而言之,“冥世偈”故事,連同“長慶二年”說,乃是一宗教傳說,信或不信,都無傷大雅;但若以之為唯一準繩,去考定其他史料的時代,恐怕是失之於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