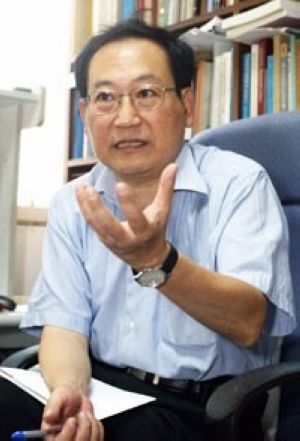你要讓身體力行 為給人食用而大量飼養動物卻不造成它們痛苦是不可能的。即使不用集約法,傳統的牧養也 使動物遭受閹割、幼獸與母親分離、社群破壞、烙印、運往屠宰場而終遭屠殺。我們很難想 象如何能把動物養來當食物而又不造成它們痛苦。如果少量飼養或許還有可能,但今日城市 吃 肉的人那麼多,又如何供應?設若以少量飼養法供應眾多人的肉食,則價格必然極高— —何況飼養動物以供應蛋白質本就已是代價極高的辦法!如果以合乎動物福利的方法來飼養 和屠宰動物,則肉品必然只是少數富裕人士的特權。 從嚴格的邏輯來說,又憐憫動物又貪吃它們的肉,也許並不沖突。你可以反對讓動物痛苦, 但如果動物自由而活,無痛立即而死,就可食其肉。但是,在事實上和心理上,又悲憐動物 又繼續食其肉卻不可能不矛盾。如果我們只為了口味而取其他動物的性命,則該動物就只不 過是我們的某種目的之手段。不管我們對它們何等憐憫,終有一天我們會把豬、雞、牛作 為我們所用的“東西”;而只要我們繼續用我們可以花得起的錢來買動物的身體為我們的食 物,你就不可能不改變它們自然的生存狀態,而我們也不會覺得那些改變有何不妥。工廠化 農場正是以動物為人類之手段而將科技施諸於它們身上的結果。我們的飲食習慣是頑強的 ,不容易改變。我們總是想讓自己相信我們可以關懷其他動物而又可以繼續吃它們。沒有一個 吃肉的人能夠毫無偏見地去判斷人類飼養與屠殺動物對它們造成的真正痛苦。 但所有這些與我們每天吃飯面臨的道德問題還沒有直接關系。理論上不管是否真可以飼養與 屠宰而不造成痛苦,我們每天吃的肉卻是來自痛苦地生、痛苦地死的動物,它們的生與死沒 有受到任何真正的關照。所以,我們必須自問的不是“吃肉‘都’不對嗎?”而是“吃‘這 塊’肉對不對?”問題這樣提出時,不管是反對對動物做“不必要的”屠殺的人還是僅反對 使動物“痛苦”的人,都會回答說“不對”。 只要大家還繼續購買集約農場的產品,一般的抗議和政治行動就不會產生重要的改革。即使 在大家以為愛護動物的英國,由於受到露絲·哈里遜的《動物機器》一書的刺激而引起廣泛 爭論,英國政府指派了一個專家委員會(布倫貝爾委員會)來調查動物遭受的虐待,並提出建 議,但在建議提出後政府拒絕執行。1981年,下議院農委會再度對集約農場做調查,這 次調查也對消除最殘忍的一些方式做出建議,可是,照樣全未實行。設若英國 的改革運動如此,則美國絕不會更好,因為美國的農業綜合企業遊說團的力量更大。 做素食者並不僅是象徵性的姿態。也不是為了在醜陋的世界中潔身自好,表示自己未參與周 遭的殘忍與屠殺。吃素是一項實際而有效的行動,志在結束對動物的屠殺與摧殘。現在,暫 時讓我們假設:我們所對的只是讓動物痛苦而非屠殺——那麼,上一章所記述的集約農場飼 養法又該如何終止呢? 這並不是說一般的抗議和政治行動無用而應放棄;不,它們是有效改變動物待遇的奮鬥中必 要的部分。在英國,像“悲憐全球牲口”等等組織,就讓公眾了解到牲口所遭受的摧殘,甚 至於廢除了小肉牛的牛欄。最近,美國的一些社團也激起大眾對集約農場動物的關切。但是 ,只有這些運動是不夠的。 那些因剝削動物而獲利的人並不需要我們的贊同。他們要的是我們的錢。出錢購買他們飼 養的動物之屍體,乃是他們得自大眾的主要支持(在許多國家中,另一主要支持是政府貼補) 。只要他們能把集約飼養法養出的動物賣掉,他們就會用這樣的方法繼續飼養,就會有足夠 的財力來反抗政治改革運動,他們也能夠振振有詞地說,他們只是供應大眾所需。 所以,我們必須拒絕吃現代化農場的動物之肉——即使你認為如果動物活得快樂、死得無痛 則食之不錯。吃素,是一種抵制。對大部分素食者而言,這種抵制是終身的,因為一旦他們 突破了以動物為食的習慣,便無法再贊同區區為自己的口味而屠殺動物性命。但抵制今日市 場肉類,主要用意不是在反對殺,而是在反對對動物的凌虐。除非我們不食其肉,否則我們 所有的人都在助成現代農場,使其繼續存在、繁榮,助成這些農場對動物的種種殘暴行徑。 是在這個地步,物種歧視與否才踏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在這個階段我們被迫驗證我們對 動物的關懷是否真切。在這個門檻,我們可以自己做一些事,而不是只說道理,只等著政客 去採取步驟。遠處發生的事,我們有立場並非難事;但在家門口,物種歧視像種族歧視一樣 就會現形。反對西班牙鬥牛,反對韓國人吃狗,反對加拿大人殺小海豹,而自己又繼續吃囚 禁籠中的母雞所生的蛋,繼續吃被剝奪了母愛的、沒有適當食物的、關在籠中不能伸腿的小 牛的肉,正像反對南非種族隔離而又勸自己鄰居不要賣房子給黑人一樣。 我們有時候會說,反正動物已經死了,我們不吃,也不能使它們起死回生,我們就吃吧!這 種借口是我經常聽到的,而且也似乎說來當真,但是,一旦我們認定不吃肉是一種抵制行動 ,則前述借口便難以成立。當抵制葡萄行動因凱撒·卡維茲的努力而釀起——其目的是為改 善葡萄採集工的薪水與生活條件——市場上仍供應由工會之外的廉價勞工所採集的葡萄;當 我們抵制這些葡萄時,並不能讓那些已采過的勞工獲得工資彌補,正如動物死不能復生,為 什麼我們還要抵制?我們要做的,不是改變過去,而是不讓我們所反對的事繼續下去。 為讓吃素的抵制涵義更有效更明顯,我們就不可羞於承認自己拒絕吃肉。在雜食性的社會中 ,素食者常被問起為什麼吃東西那麼古怪?被人這樣問時,可能很氣惱,甚至很窘;然而 ,這卻是好機會可以讓人知道他們所不曾覺察的殘忍。(我第一次聽說工廠化農場,便是經 由一位素食者;他很有耐心地告訴我,他為什麼吃得和我不一樣。)設若唯有不吃肉才能 終止對動物的殘暴,則我們就必須鼓足勇氣,讓參與抵制的人盡量增加。但要想抵制有效, 我們自己卻必須以身作則。 我對素食的抵制涵義既然這般強調,有些讀者不免會問,如果抵制的效果不彰,則素食還有 什麼必要性呢?我的回答是:一件我們認為該做的事,在未能確定其是否成功以前,往往必 須堅持;任何反壓迫、爭正義的偉大運動,如果領導者必須確定其成功才做努力,便永不可 能存在。所以,如果只因素食目前效果不彰而加以反對,則不成為反對理由。何況,素食運 動即使就整體而言尚未成功,但個體的行為確實已有一些成效。蕭伯納曾說,他死後送葬的 隊 伍中將有成群的豬、牛、羊、雞和大群的魚,這些動物都因他是素食者而免遭殺害。雖然我 們不能指認哪一隻動物是因我們吃素而未遭殺害的,但我們可以相信,我們自己的不吃肉食 加上原已就有的不吃肉食者的行為,對現代工廠化農場飼養和屠殺的動物數量一定有所影響 。需求量少,價格就低,利潤便少。利潤越少,則被飼養與屠殺的動物也會隨之減少。這隻 是初級經濟學,而且我們可以在肉雞期刊上看到這樣的報表:肉雞的價格跟雞棚中無歡的雞 ,數目關系密切。 再者,吃素還有一層特殊的意義,就是以身體力行的方式駁斥了常見的而又根本錯誤的工廠 化農場辯詞。因為,有些人竟然說,工廠化農場是解決世界飛漲的人口食物之道。這種說法 真 是荒謬無比,以致我必須在此對糧食問題做一簡述——僅管它跟本書所強調的動物福利沒有 直接關系。 所以,素食比一般的抵制更有意義。為反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而抵制南非產品的人,除非迫 使南非做了政治改革,就什麼也未達成(但不管成果如何,這種抵制都是應該的);但素食者 卻不管能否目睹點燃廣大的拒吃肉食運動,從而終止農場的殘暴行為,他都知道他自己的吃 素可以減少某幾隻動物的飼養與屠殺。
THE END